夜色(1998-1999刘庆邦短篇小说) 9787532164417
举报
全新正版 可开票 支持7天无理由
-
作者:
刘庆邦
-
出版社:
上海文艺
-
ISBN:
9787532164417
-
出版时间:
2018-07
-
装帧:
其他
-
开本:
其他
-
ISBN:
9787532164417
-
出版时间:
2018-07
售价
¥
19.03
4.8折
定价
¥40.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4-01-21
卖家超过10天未登录
手机购买
![]()
微信扫码访问
-
-
商品描述:
-
目录
\"目录
晚上十点:一切正常
喜鹊的悲剧
外衣
发大水
春天的仪式
五分钱
一个聪明人和一个精神病患者
一篇小说的故事
梅妞放羊
不是插曲
美少年
草帽
谁家的小姑娘
大姐回门
毛信
青春期
躲不开悲剧
天凉好个秋.
拉网
夜色
内容摘要
短篇小说集。这是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卷之四,收录了作家1998-199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刘庆邦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又开始偏重乡村题材,与前期的乡村题材的创作不同,作家这一时期的乡村题材创作不再停留于对乡村故事的讲述,而更注重对乡村记忆的深入解剖,对美丽人伦的眷恋,对伤害与丑恶作着反思,尤其是《五分钱》这样的作品,呈现出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的子午反省精神和对弱者的悲悯情怀。
精彩内容
\"夜色有了对象以后,周文兴变了,变成一个有心人了。他家菜园子的篱笆不知被谁家的猪拱开了一个口子,他拿来一些剥去麻皮的新麻秆儿,很快照原样把篱笆修补好了。菜园子的事情以前归父亲和哥哥管理,他只知道吃黄瓜,吃辣椒,才不管猪呀羊呀进来不进来呢!现在不了,他一眼就看见了篱笆上的口子。菜园子里有包头白菜,还有刚长成的萝卜,他不允许丑嘴丑脸的猪猡钻进来随便糟蹋。他把麻秆儿的根部斜着埋得比较深,麻秆儿相交之间编成网眼样的菱形。这样一来,篱笆就似乎变成撕不破的网了。他扎的篱笆跟父亲春天时扎的篱笆衔接得很好,只是父亲扎的篱笆经过雨淋日晒变黑了,他补上去的篱笆是崭新的,在秋阳下闪着耀眼的银光。
周文兴家菜园子的地头紧挨着一条小河沟的里侧,沟里的水不多了,两边的坡度也缓缓的。一个小孩子若从对岸沟坡跑下来,跃过那点浅水,能一气冲到里侧他家菜园子里。周文兴把一张铁锹打磨得利利的,一锹一锹把里侧沟坡的肥泥斩下来,自下而上帮在菜园子的边上。他这么干是一举两得:一是把沟坡弄陡了,跟堑壕一样,对菜园子起着保护作用;二是把菜园子的地帮宽了,来年多种一两畦菜不成问题。干这个活儿不是说话的,一锹泥重似一块土坯,每往上甩一锹都需要力气,更需要耐心。他的脸绷劲绷得红红的,背上胳膊上冒出不少汗。有一块云彩在他头顶的天空停下了,他一会儿也不停,把胳膊上的汗水甩得直往上飞。村上的人从河沟外沿路过,见周家的二小子干活儿这样卖力,就跟他打招呼,让他慢着点干,别累着。周文兴笑笑,说没事儿。村上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周文兴订下对象的事,对于周文兴如此肯干,他们没有把周文兴和他的对象联系起来,没有从对象身上找原因。但他们确实看出了周文兴的变化,这小子,说变突然就变了,变得像个过日子的人了。他是凭什么变的呢?
周文兴把裤腿挽得高高的,是赤着双脚刨沟泥,脚上沾的又是泥又是草的。干完活,他把脚洗得干干净净,穿上鞋,把裤腿放下来,才往村里走。走到半道,他摸到额头上有干泥点子,便返回菜园子,从井里提上一桶清水,把脸、脖子和耳朵都洗了洗,才回家去了。这表明,周文兴不仅在干活方面按有了对象的标准要求自己,对自己的形象也比较注意了,也把标准提高了。
儿子有什么变化,当然瞒不住父母的眼睛。近来周文兴的父亲和母亲常常相视一笑,笑得有些会心。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儿子到了十八九,该找对象就得张罗着给他找对象,你一天不给他订下一个对象,他就老也不长心,一天到晚吃凉不管酸。他把对象找准了,把亲事订下了,转眼间就像变了一个人。打个比方不好听,小伙子的对象好比是副牛马套,小伙子一旦有了对象,不用别人牵着赶着,他自己就乖乖地上套了。周文兴的父母没有把他们的看法对周文兴说出来,儿子大了,有些话要说三分,留三分,还有三分待思忖,说透了儿子会不好意思。父亲夸周文兴把篱笆补得好,结实。父亲还说,他也想过刨沟泥帮帮菜园的边子,只怕气力跟不上趟儿。现在二小子行了,比老子强了。母亲呢,周文兴一回到家,母亲就让他快歇歇去吧。或者告诉他锅里还有什么饭,让他吃了先垫垫底儿。有一天早上,周文兴刚扫完院子,父亲跟他说,等过罢年,到窑上买些青砖,再到河坡里起些草坯,把外包青的房子盖起来,就可以给他办事了。父亲说的给他办事,就是指给他娶媳妇,让他完婚。父亲跟他说这话时,母亲也在场,母亲的眼睛一直看着他。这番话,大概就是父母要对周文兴说出的那三分话,周文兴一听就明白了。父亲说出的话是三分,周文兴顺着话意往前发挥了一下,发挥到七分八分,他点点头,脸有些红了。
周家为周文兴盖房子的事尚在筹备之中,周文兴听说,高玉华已经开始和泥脱坯了。高玉华是高家庄的,就是周文兴的对象。把高玉华说成是周文兴的未婚妻也可以,只是未婚妻的说法太书面化了,当地人认为是拽文,都说不出口。就连对象这种词儿,上点岁数的人也很少说,需要对周文兴提到他的对象时,他们称为高家庄的那闺女。这种称谓是有点长,但因为是一个特指,周文兴绝不会听错。不论什么事情,短了不见得就好,长了不见得就不好。比起“未婚妻”和“对象”,周文兴最喜欢“高家庄的那闺女”这个称谓。他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反正一听人对他提到“高家庄的那闺女”,心中就生出一种悠远的情思,全身心都美得很。周文兴所在的庄子离高家庄不过二三里,唱一支歌的工夫就走到了。他们庄的人去镇上赶集,都要路过高家庄的村头。是赶集回来的人把看见高玉华在村头和泥脱坯的消息报告给周文兴的。报告消息的人使用的当然是报告好消息的口气,报告完了就看着周文兴乐,看看这十八九岁的哥哥反应如何,能不能把得住满心的欢喜。对周文兴来说,凡是高玉华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听到有关高玉华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气得不行。但他表面上装作这消息很平常,不敢流露出过多的欣喜,更不敢多打听,只微微一笑就拉倒了。
周文兴难免要对得来的消息想了又想,高玉华干吗要脱坯呢?他们家大概要翻盖房子。常言说脱坯搭墙活见阎王,脱坯是重体力劳动,是男人们干的活儿,高玉华一个闺女家,细手小肩膀的,怎能承当得起呢!可是,高玉华的母亲是小脚,父亲身体不好,她弟弟正在学校读书,她在姐弟中间是老大,她不干谁干呢!想到这里,周文兴心上渐渐沉重起来,像是压了一块湿坯。
当然了,高玉华舍己为人的精神也的确让周文兴感动。你想呀,高玉华跟他已订了亲,过个一年半载,他盖好了新房,就要把高玉华娶过来。高玉华虽然翻盖好了房子,却不是为自己住,是为弟弟成家创造条件。高玉华呀高玉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这天吃过晚饭,周文兴一个人悄悄地出了村,往集镇的方向走去。若有人碰见他,他就说到镇上看望一位同学。没有碰见
他呢,他就去看望高玉华脱出的坯。他要证实一下,高玉华是不是真的脱坯了,脱出了多少坯。天很黑,没有月亮,只有星星。
星星的光是散光,老也不能照下来,照了一万年还是个星星。地里高秆儿的庄稼都收割完了,种上了小麦。在白天,能看见小麦刚钻出鹅黄的细芽,晚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知谁家在麦地里晒了一片红薯片子,使黑黢黢的田野里总算有了一些淡淡的白光。要是外地来的过路人,不会想到那是红薯片子,会以为那是一汪秋水。凭着虫鸣的声音,他大致能分辨出地里还有一些红薯和红萝卜没有收完,那是生命短暂的秋虫们最后的栖身之地。在寂静的夜晚,秋虫的鸣叫平地而起,密度和力度都很大,颇有些压倒一切的悲壮。给人的感觉,秋虫们像是整肃地站在舞台上,肩并肩,手挽手,在不倦地对大地歌唱。唱到动情处,它们一个个泪流满面,不能自制。但它们没有一个擦眼泪的,就那么忘我地唱下去。这说明天还没有下霜,等严霜一打,秋风一吹,红薯和红萝卜叶子就会发蔫,变黑。旦夕之间,秋虫就销声匿迹,不可寻觅。周文兴在路上没碰见一个人,就来到了高家庄。高家庄四周有护村的海子,东海子外沿是一个打谷场。周文兴估计,高玉华脱坯只能在打谷场上脱。他从官路上拐进打谷场,蹲下身子一瞅,见场里果然脱的有坯。他先是看见一两块,后来越看越多,黑压压一片。坯们排列得很整齐,站是方,立是正,没有一块乱说乱动的。周文兴心说,这些坯都是高玉华一块一块脱出来的呀!他仿佛看见,高玉华正蹲在打谷场的地上,左边一堆泥,右边一盆水,面前放着一个木制长方形的坯模子。高玉华双手把和得很到家的泥坨子搬起来,摔进坯模子里。她把坯模子里摔得满满当当不算完,还要把泥往四个角里充塞,充塞得到边到角,不留一点空隙。为了让坯面光滑平整,高玉华在水盆里湿了手,在坯面上抹,然后拿竹匹子贴坯模子的上沿平着一刮,将空底的坯模子框架往上端起,一块四角四正的泥坯就脱颖而出。干这样重的活儿,高玉华难免要出汗。她一低头,汗珠子就落在坯面上了,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泥水。她前面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了,贴在了眉上。她勾起了小指,把湿得打缕的头发抿在耳后。她的小指上也是沾了泥的,手指在额头上一走,指尖上的黄泥就留在那里了。高玉华脸上沾了泥不但不丑,反而显得更好看了。周文兴不知不觉朝面前的一块坯摸去,坯出自高玉华的手,他似乎在坯面上感到了高玉华的手温。到目前为止,他还从未摸过高玉华的手,那么,就算这块坯是一个中介体,他摸到高玉华留在坯面上的手迹,就等于接触到高玉华勤劳而美丽的小手了。要不是坯还湿着,还撑不起身子,他真想把坯抱起来,嗅一嗅坯上的气息,把坯面在自己的脸上贴一贴。这样想着,他扭过头往打谷场边上瞅,看看是否有人注意他心中的秘密。打谷场边有几棵小树,那黑色的轮廓很像几个人在观察他,并不时对他发出窃笑。周文兴断定那是一些小树,但他的手还是从高玉华“手上”收回来了。
看了高玉华脱出的坯,他又悄悄来到海子边,看高玉华和泥的地方。他们这里和脱坯用的泥,一般都是就着海子边挖一个池子,用钉耙将海子边的泥土翻起来,泼上水,撒上麦糠,赤脚跳进去用脚踩。一池子泥,起码要用钉耙扒三遍,用脚踩三遍,泥才能和出黏性来,生泥才能和成熟泥。这样累人的活儿,不知高玉华怎能吃得消!周文兴没看见过高玉华的脚,更没看见过高玉华的小腿。可他相信,高玉华的脚和腿肯定都是又细又白的。而泥土很粗,麦糠是涩拉拉的。用那样的腿和脚来踩泥巴,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高玉华跟他订过亲了,高玉华的腿和脚就不再是高玉华一个人的。他不敢说高玉华的一切是属于他的,但他总觉得自己对高玉华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对高玉华的腿负有一定责任,对高玉华的脚也负有责任。别的大话他不敢吹,等高玉华和他结了婚,他敢打包票,像这样赤脚光腿的粗活重活,他绝不会让高玉华干。周文兴伸头往池子里看,见池子里泥没有了,麦糠也没有了,池底只有一点灰白的浅水。个把星星映在浅水里,若隐若现的。周文兴知道,高玉华明天还会来这里和泥,还会弄得满身汗满脚泥的。要是这里有钉耙,有麦糠,他真想下进池子里,把池底的泥土翻起来,替高玉华把泥和好。那样的话,高玉华就省力多了。
海子里沿传出了说话声,周文兴的心跳不由得有些加快。虽然天黑得不见人影,但他听出来了,说话的正是高玉华。像是有一个妇女到高玉华家串门,向高玉华家借一样东西,高玉华就把人家让进屋里去了。高玉华的家就在海子里沿,三间堂屋,两间灶屋,都是草顶土坯房。他和高玉华第一次相亲,就是在高玉华家的堂屋里。高家庄庄前有桥,庄后有桥。媒人领着他,从庄后的桥进的庄子,而后七拐八拐,来到了住在海子边上的高玉华的家。高玉华从里间屋一出来,媒人让他们俩谈吧,撇下他俩就出门去了。那天周文兴心情紧张得很,心跳得不知说什么好,也不敢多看高玉华几眼。好在他的村子和高玉华的村子相距不远,以前在大队开会和去镇上赶集,他都见过高玉华,而且知道了高玉华的名字叫高玉华。他是从村里年轻姑娘们的口中得知高玉华的名字的,那些姑娘都认为高玉华好看,脸好看,腰身好看,干起活来也好看。后来再见到高玉华时,他就比较留意,觉得高玉华是挺不错的。他对高玉华早就很满意了,来相亲只不过是走个形式。他怕一句话说不好了,给高玉华留下不好的印象。那天先开口说话的是高玉华。高玉华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理解高玉华是让他表态,他上来就说,他没意见。没意见就是同意。高玉华说,她也没意见。就这样,相亲的形式就算走完了,终身的大事就算订下了。高玉华说完了没意见,就站起来出门去了。高玉华往外走的时候,他才大胆地从后面看高玉华。给他的印象,高玉华长得很瓷实,走路是很有劲的。他俩相亲是在春天,现在到了秋天。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他俩再也没到一起单独交谈过。两个人越是不能到一起,周文兴对高玉华的思念越热切。可以说高玉华已占据了他的心,他没有一天不想念高玉华,每天都在肚子里念叨高玉华好多遍。一想到高玉华,他就像犯病似的,心里柔软得不行,愁得不行。他老是担心高玉华是一种缥缈之物,老是担心不能与高玉华结合在一起。听见了高玉华的说话声,他心头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觉得踏实多了。串门的妇女从高玉华家出来了,高玉华把人家送到院子里,她们又说了几句话。那个妇女问高玉华,坯是不是脱够了。高玉华说没有。周文兴没有想到,那个妇女竟提到了他。妇女提到他当然不是直接提他的名字,而是他的一个代名词——周桥的那个人。妇女问,咋不让周桥的那个人来帮你脱呢?这个问题比较重大,不知高玉华如何回答,周文兴两个耳孔张得圆圆的,生怕听漏了一个字。结果呢,高玉华什么也没回答,高玉华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周文兴回到家,高玉华的叹气留在他心上,跟他一块儿回了家。周文兴怎么也想不明白,高玉华叹气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人遇到了无可奈何的事才叹气,发愁时才叹气。看来高玉华是遇到了无可奈何的愁事了。倘是高玉华为脱坯的事犯愁,他倒是很乐意替高玉华消愁。只要高玉华让媒人给他捎个口信儿,他马上会赶到高家庄,把和泥脱坯的事全部承担下来。一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就去帮对象家干活,会引起一些人的笑话。为了高玉华,他顾不得那么多了。可是,如果高玉华一点口信都没捎,他就贸然到高家庄帮高玉华脱坯,是不是显得太唐突了。周文兴左想右想没什么好办法,他自己也快要叹气了。情急之中,他又想到应该把这件事情跟父亲透露一点,父亲也许会帮他想些办法。他没跟父亲说脱坯的事,说的是起坯的事,问父亲准备到哪里起坯。脱坯和起坯都带着一个坯字,他想父亲应该明白他的话意。父亲大概真的老了,他说的是起坯,父亲也只往起坯上想。父亲说,他已经看准了一个起坯的地方,在南河坡,马上带他去踏看。他随父亲到南河坡一看,那里不光坡度平缓,草地也厚,的确很适合起坯。起坯跟脱坯不同,起坯是利用现成的草地,推动石磙把草地碾平碾实,用带木柄的单刃离刀,纵横着把草地离成坯块大小的长方格,然后用专用的起坯铁铲,一块一块把坯铲起来。起坯的活儿是一种集体性的劳动,一个人是干不成的。比如用离刀打方格时,需一个人扶刀柄,还要两个人用绳子把插进草地的离刀往前拉。用铁铲铲坯时也是一样,至少需要三个男劳力协同劳动。别人家在草地上起坯时周文兴去看过,当铁铲把草的根须切断时,一路发出“切切割割”的声音,相当好听。起的坯要比脱的坯结实,耐用,因为起的坯里面的草根密密麻麻,柔韧自然,把泥土都抓住了。起的坯不仅能盖房用,垒露天的墙头也可以,抗得住雨淋。谁家的墙头绿茸茸的,那准是坯里面的草根经春风一吹,又生芽了。时间久了,草根不再发芽也没关系,常见一些草坯被大雨淋得草根裸露出来,支乍得跟刺猬一样,也不会散架。周文兴还得把话题往脱坯上引,他问父亲,是起的坯结实还是脱的坯结实。这话显见得是明知故问了。这次父亲微笑之后,把二小子的心思说出来了。父亲说,他想让周文兴去帮人家脱坯,让媒人带去了话,人家怕周文兴害羞,又怕累着周文兴,回说免了。父亲又提议让周文兴的哥哥到高家庄帮着脱坯,高家庄的那闺女也没同意。高家庄的那闺女真是要强得很,说她自己什么都能干。父亲的话让周文兴顿感羞赧,原以为父亲只管自家起坯,不管人家脱坯,不料他想到的,父亲替他想到了,他没想到的,父亲也替他想到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好父亲。正如父亲所说,高玉华是够要强的,他对高玉华的佩服又增加了几分。不过,他也有些隐隐的心疼:你怕累着我,难道就不怕累着你自己吗?你要是累伤了身体怎么办?
周文兴和父亲出了河坡往村里走时,路上碰见几个背书包的小孩子。其中一个小孩子指着周文兴,把周文兴喊成高玉华。他们这里就是这样,对那些订过亲但尚未结婚的青年男女,喊笑话时愿意把女的名字安在男的身上,把男的名字安在女的身上,来个交叉换名。如同把周文兴喊成高玉华,也会有人把高玉华喊成周文兴。没人说得清这种故意张冠李戴的喊法有什么深意,却往
往能收到不错的效果。周文兴也是这样,听见有人把他喊成高玉华,他的样子像是有些生气,做出凶恶的样子向小孩子追过去。
他这一追不要紧,孩子们觉得好玩,一齐把他喊成高玉华。他再追,孩子们再跑。他一停下,孩子就回过头冲他喊。孩子们把高玉华喊得整齐划一,节奏感很强,声音也很洪亮。要是让他们朗读课文,恐怕他们不会这么来劲。在落日的余晖里,他们脆朗的喊叫像云雀一样布满天空。其实他们上了周文兴的当了,周文兴一点也不生气,孩子们把他喊成高玉华,等于向全世界宣传他和高玉华跟一个人一样,他小子心里幸福得很哪。
晚上,周文兴睡不着觉,听见嫂子一会儿就笑一下。哥哥在外当兵时,他和父母住堂屋,父母住里间,他住外间。哥哥复员回来和嫂子结婚后,父母搬到灶屋去住,他和哥嫂住堂屋,哥嫂住里间,他还是住外间。没有和高玉华订亲之前,他不好好在家里睡。夏天,他到打麦场里睡,或者到瓜园里睡,那里比家里凉快。冬天,他抱起被子到饲养室的草屋里睡,那里集合有一些年龄相仿的伙伴,比家里热闹。自从有了高玉华作对象,他就自我约束起来,不再到处乱睡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了,是一个将要做男人的人了,处处要稳当些,守不住家是不行的。至于结婚后怎样做男人,他还没有一点经验,尚不知从何做起。哥嫂住的里间和外间只隔一层箔篱,哥哥倒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他不打算向哥哥学习。哥哥和嫂子在里间屋住了不到两年,两口人就变成了三口人。这说明哥哥对嫂子,怎么说呢,不够爱惜。要是他和高玉华结了婚,顶多把高玉华拥抱一下就满足了,他才舍不得对高玉华怎么样呢!想到把高玉华拥抱一下,他怀里就温温润润的,似乎真的把高玉华拥抱到了。他开始在心里轻轻地呼唤高玉华的名字,先是唤三个字,后是唤两个字,再后只唤一个字。字唤得越少,他心里越颤颤。当只唤一个字时,他还对高玉华说了话,他说的是对不起,对不起。身下的床箔响了一下,他一时吃不准声响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不知是自己的动作失了分寸,还是说话走了声。他不敢再瞎想了。嫂子又笑了,笑着还说滚蛋滚蛋。嫂子也许让正吃奶的小侄子滚蛋,也许让哥哥滚蛋,他们总是在玩好玩儿的名堂。
哥哥和小侄子都没滚蛋,他却从床上爬起来了。他有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的方向是高家庄,是高玉华脱坯的地方。好像那些坯是高玉华派出的代表,那些代表正列队欢迎他。这次周文兴没有白来,一摸到坯他不禁有些欣喜。先一天脱出的坯已经半干,这些坯需要一块块侧立起来通风和晾晒。他搓了搓手,高兴得想大笑一下,想说他总算找到活儿干了。他没有笑出声,也没说出声,只是把高兴的表情在黑夜里夸张地演示了一下,就开始做翻坯的工作。他一上来干得太慌张了,头上出了一头汗,背上也汗浸浸的。他对自己说,不要着急,不要慌张,不会有人看见的。安慰了自己,他的心情才平稳些,翻坯也不那么手忙脚乱了。每块坯搬起来,下面都有一块湿印。他把坯侧立在一块干地方,躲开那个湿印。他把侧立的坯立得稳稳当当,排列得整整齐齐。他要让高玉华知道,他是很会干活的。按他的想象,高玉华明天过来一看,见半干的坯们侧立起来了,也许会吃一惊。但吃惊过后,高玉华一定会想到是他周文兴帮着干的。他不想着让高玉华感谢他,只让高玉华知道他对高玉华的一片心意就行了。这么说来,周文兴把每一块侧立的坯都当成一个信使,他通过每一个信使向高玉华转达他的心意。谁说坯是泥巴做的就没心没肺,原来一块生硬的泥坯也能寄托柔软的关爱之情。周文兴一旦找到了寄托就不愿放过,他接二连三地在夜里帮着高玉华翻坯。高玉华白天脱坯,他夜间翻坯,谁也不知道一对未婚的青年男女有这样美妙的配合。
打谷场边有一个麦秸垛。这天晚上,周文兴正翻着坯,听见麦秸垛那边响了一下,像是有人碰到了麦秸垛。他一惊,又一喜,想到躲在麦秸垛那边的人一定是高玉华。他帮高玉华翻了坯,高玉华会看到的。高玉华不会认为是画中走下来的人帮她干的,不会认为是神仙干的,高玉华不用怎么想,就会想到是他周文兴。想到不等于看到,高玉华要证实一下夜间翻坯不留姓名的不是他是谁,就悄悄躲在麦秸垛一角观察他,肯定是这样的。周文兴的心花开得有些大,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想走到麦秸垛那边去,给高玉华创造一个条件,让高玉华近距离地看到他。另外,高玉华大约已经看见他了。可他还没看见高玉华,他要证实一下,把麦秸垛碰得发出响声的到底是不是高玉华。没有马上到麦秸垛那边去,是他有点犹豫,怕吓着了藏在麦秸垛拐角的那个人。这天晚上是个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往哪儿看都是黑的,比前几个晚上都要黑。空气有些泛潮,随手抓一把都黏乎乎的。这潮气似乎增加了夜色的密度,使夜的黑暗有了水样的质感。随着秋天的不断加深,夜间有些凉了。这凉仿佛是夜间的一部分,跟夜色有着同样的性质。白天,周文兴随着人流去镇上赶集时,特别注意了一下打谷场和打谷场周围的景物。南边是一块麦地,东边是一块红薯地。场边长着几棵小树。场里有一个麦秸垛,还有一个暗红色的石磙。他把这些景物都记在心里了。除了高玉华亲手脱出的坯,他对每样景物也都有了好感。这些景物对他和高玉华的默契配合起着见证作用,又为他们守口如瓶似地保着密。在夜里,这些景物大都看不见了。麦秸垛的体积比较高大,还朦朦胧胧看得出大致轮廓。他们这里是大平原,没有山。麦秸垛就算是他们这里的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山的作用是遮挡和隐蔽。麦秸垛在千里平原上起着山的作用,很多有趣的故事都是在麦秸垛那里发生的。周文兴暂时停止了翻坯,一心往麦秸垛那里望着,倾听着。他没有再听见麦秸垛那边发出声音。这使他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是麦秸垛后面的人已经走了。他不再犹豫,站起来,向着横卧的山脊一样的麦秸垛走去。他刚走近麦秸垛,一个黑色的人影就从麦秸垛头转出来了,快步向打谷场空旷的地方走去,发出细碎的脚步声。尽管周文兴心里是有准备的,他还是稍稍地吓了一跳。他没敢向人影跟过去,不知所措地站下了,那个人影也站下了,向周文兴转过身来。深重的夜色中,两个黑黑的人影形成了一种对峙的局面。周文兴的心跳得腾腾的,夜色脚下发软,怀疑自己是在梦中。夜太黑,他看不清对面那个人影的面目,但是凭感觉,他断定那是高玉华。夜色勾勒出高玉华的身影,身影是模糊的,几乎融入夜的背景,这使高玉华看起来虚幻而美丽。遍地的秋虫还在鸣叫。这种整体性的鸣叫一点也不间断,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虫子在鸣叫,而是大地本身发出的呼
吸。大地吸得深沉,呼得也深沉,夜空显得更加沉静。这时周文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渴望,他想接近高玉华,喊一声高玉华的名字,跟高玉华说几句话。只有这样,高玉华才是真实的,这个夜晚才是真实的,才会在他心上留下永久性的记号。然而,他没有喊出声,只是咳了咳喉咙。当他向高玉华接近时,高玉华又向前走去。他舍不得高玉华走,只得站下。只要他站下,高玉华就站下。他们就这样在夜幕下走走停停,没有接触,也没有分开。在走动中,周文兴嗅到了高玉华的体香。停下来时,周文兴听到高玉华有些急促的呼吸。高玉华还咳嗽了一下,她咳得轻轻的,像是用咳嗽告诉周文兴,她真的是高玉华。
天边打了一个露水闪,闪不大,一闪就过去了。但这个闪还是把高玉华照耀了一下。高玉华有些出乎意料似的,转过身走了。这次她没有再停下来。
周文兴回到麦秸垛那里,靠着麦秸垛叹了一口气又一口气,一次比一次叹得长。正叹着气,他突然想到,那些已经晒干的坯该垛起来了,不然的话,万一天下了雨,那些坯有可能被淋坏。
说干就干,他马上垛坯...

![]()
孔网啦啦啦啦啦纺织女工火锅店第三课
开播时间:09月02日 10:30
即将开播,去预约


直播中,去观看

 占位居中
占位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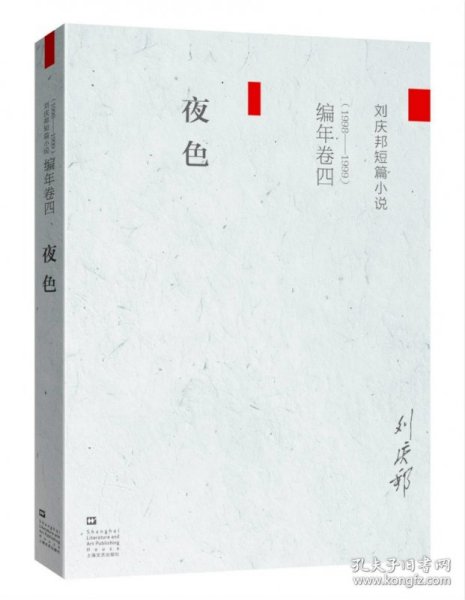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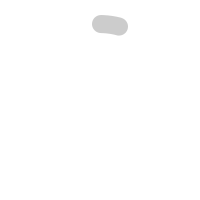

 直播中,去观看
直播中,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