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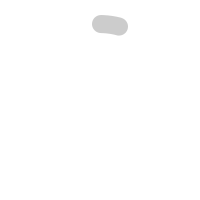
- 商品详情
- 店铺评价
-
图书条目信息

展开全部
- 货号:
- 8366144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佟进军编著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锡伯族卷)》是该作品集之一。
目录
序佟进军 / 1
小说
猎人吴文龄 / 3
别了,噬人的梦关荣 / 20
“朱伦”念说家佟加·庆夫 / 77
系在牛尾巴上的故事觉罗康林 / 90
在那遥远的国土上佟加·庆夫 / 106
西陲碣石吴文龄 / 122
锡伯族风俗小说佟林清 / 152
寂静的雪野傅查新昌 / 170
神奇的丁香花铁木尔·关清福 著苏永成 译 / 182
旧事雷志芬 / 199
时光掠影郭美玲 / 208
远行的绿卡车赵春生 / 214
美丽的复仇何久成 / 222
散文
忆启蒙者们(外一篇)郭基南 / 233
火州采风记忠录 / 249
古柳杨震远 著佘吐肯 译 / 255
再见,伊犁拙木豪格 / 258
啊,达子香你为什么悲伤王绍枫 / 270
苦丁香何久成 / 273
关于城墙的记忆赵春生 / 280
酒润关东(外一篇)佟伟 / 282
回望时光深处佟志红 / 291
马儿跑过我的心境觉罗康林 / 299
诗歌
岁月(外三首)郭基南 / 313
小毡房,你好(外二首)哈拜 / 320
金桥颂乌扎拉·舒慕同 著佘吐肯 译 / 324
察布查尔畅想曲(外一首)佘吐肯 / 327
布哈(外四首)金生 / 338
猎人之歌吴文龄 著金石 译 / 343
灵魂面对灵魂(外二首)阿吉肖昌 / 346
读郭基南诗集《心之歌》题咏(外三首)佟兆飞 / 355
梦回锡伯家庙(外三首)吴明政 / 358
月光依旧是月光(组诗)郭晓亮 / 360
醒了,嘎善(外三首)安鸿毅 / 366
和一种情绪握握手(外一首)拙木豪格 / 373
牛录(外四首)阿苏 / 384
察布查尔(外二首)西榆 / 397
锡伯族之歌(外一首)顾伟 / 402
渔猎(外三首)承志 / 408
爱是四季(外四首)佟志红 / 413
我等你很久了富秀兰 / 418
嘎仙洞前有条河(外一首)王绍枫 / 420
长篇作品存目/ 422
后记/ 424
内容摘要
猎 人
吴文龄
清晨,一阵激情欢快的牧歌荡出染翠的幽谷,渐渐飘入山腰的雪白毡房,把我从甜蜜的梦境中轻轻唤醒。我微微抬起头,睁开惺忪的眼睛向毡房门外望去,只见一轮红日早已笑盈盈地在雪峰间露了脸。我急忙起身披衣走出门,迎面扑来轻柔的微风,不由得使我深探地吸了一口湿润凉爽的空气,仅存的睡意顿时烟消云散。我仰起头,揉揉眼,贪婪地极目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大自然的壮丽景象:五光十色的霞光照射着片片层云,辉映着还没消雪的座座峰峦;乳白的晨雾袅袅升腾,像轻纱般地缓缓向千奇百怪的巅峰飘去,平添一层神秘的色彩,显得格外肃穆和秀丽。雄踞群山中的腾格里白峰,披着一身银白的盔甲,宛若一尊出征的武士,威严地直逼前方。山坡上,在片片白雪的点缀中,一排排,一行行排列整齐,挺拔有力的松柏,如千军万马静候号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深谷里,从岩层汇集而成的涓涓雪水,穿过荆棘,绕过红柳,在乱石中渗透着、流淌着,犹如初次去约会的嫩妹,羞羞答答、躲躲闪闪,从百草下面掩面而过;几只觅食的苍鹰在山顶上回旋着,展开一伸不收的翅膀悠闲地翱翔着……我禁不住从心底油然腾起一股灵感的激情,不由得脱口而出:
“啊!大自然,世上的能工巧匠,谁能敌日月的造化!祖国的山河,不就是一幅神笔点奇、浓淡相趣、令人神往的画图吗?”
“哈……真不愧是文人哪!”我正沉浸在兴奋中,突然从背后传来一阵粗犷的、熟悉的笑语声。我本能地转过身去:
“好呀,您这不讲交情的路友,为何不叫我一声就一个人溜了?”
“噢,”来者长长地啧出一口热气,“您经常不骑马,昨天又在马背上摇摇晃晃地赶了一天的路,我怎么能忍心把您从美梦中拉出来呀!”
我心里一喜,急忙投去感激的目光,向他点头,问:
“我们几时出发?”
“喝点奶茶就备鞍,怎么样?”他狡黠地朝我看了看,见我不吭声,“是喽。趁着早晨的凉爽赶程,人不乏马不累,不怕中午炙烤啰!”
“好的,我们争取上午赶到,可以吗?”
“不过,越往前路越不好走,您多注意。”
“听您的。”
……
山路,弯弯曲折,坎坷峭陡。穿过深谷,盘着山腰,绕着怪石,我们小心驾驭着坐骑,一步步、一阶阶艰难地向山顶攀援,渐渐进入白云深处。两匹马虽然鼻喷粗气,奋力向上,但总觉得移步不前,慢慢腾腾。有时,偶尔抽一重鞭,马被逼得四蹄错落,火花迸溅,蹄声铿锵,震荡山谷。托克托拜——我的路友,这见面仅仅两天的哈萨克汉子,把宽檐的毡帽低低地拉在眉毛上,不时地眯起眼睛向前面眺望,好像在辨认什么,又像在仔细地察看一山一石,一草一木是否有什么变化。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忽然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从侧面细细地打量起他来:托克托拜是个魁梧的汉子,他那匀称的粗壮的躯干和宽阔的肩膀告诉我,他生就一副强健的体格,能经受游牧生活的艰苦和风雨的变化;他那酱红油亮的肤色从棱角分明的脸膛蔓延到脖梗儿,洋溢着无限的活力,是阳光多年的杰作;而那浓重的眉毛下深嵌的一双黄珠中透蓝的眼睛,犹如两泓碧潭,深不可测。也许是长年累月游牧生活的缘由吧,他不管天气冷热总不愿解去腰上紧紧围裹的黑布腰带,哪怕是一刻钟。我心中笑了笑,磕了下镫,又回味了一下自己的评价,咳了一声,问:
“托克托拜同志,您在想什么呢?”
他转过身来,瞥了我一眼,说:“每年春天转场到山上,来回走过这里,就会思念我的好友。”
“嘿,您的哪位至交缘何给您留下这么深的印象?”我深感兴趣地追问了一句,“可以告诉我吗?”
“是一位锡伯族朋友。”托克托拜背过身去坦然地说。
“锡伯族朋友?是谁?干什么的?”我出于职业习惯,不管他乐意不乐意,紧追不放。
托克托拜侧目看了一眼我急切的样子,缓缓地转过身去,稍抖缰绳,顺手给坐骑赏了一鞭,眼望着前面,好一阵才开了口:
“是啊,是一位锡伯族朋友,他叫伯奇春。”
“伯奇春?……”我顿了顿,“早就听说过,可惜,还没见过面。”
“噢,您在哪里听到过他的名字?”
“好像是前年的事,”我抬头想了想,“对,是前年的事,我初来金泉公社采访时,从许多人的嘴里听到的。”
“您采访了些什么呢?”
“听说伯奇春是有名的猎手,所以,我曾去找过他。遗憾的是,未能与这位猎手见面。……可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从别人嘴里已经听到了关于他的许多有趣的事。”
托克托拜在马背上一颠一颠地听完我的话,深有感触地说:
“是啊,伯奇春不仅仅是位猎手,而且是个心地广阔、卓有远见、尊重情谊的好人。在他身上闪耀着锡伯族人那种正直、剽悍、聪慧的美德。……”
没想到他与伯奇春竟有如此深厚的情谊。我情不自禁地打断他的话,问:“您怎么如此熟悉他呢?”他好像没听到似的缄口不言了,我急得大声问:“咳,您怎么不说话了?”
“噢……”他勉强地笑了笑,“说来话长啊,您想听?”他斜睨一眼,见我点头,说:
“好,我给您讲讲。”
“那太好了,说说话倒叫人快活,不然,这么远的路,叫人寂寞、想瞌睡。”
“不过。我的口舌笨,在记者面前更难开口,叫您听起来费劲。”
“不,不,您别客气。随便说,想说什么说什么。”
“那就聊聊。”托克托拜说着顺手把马缰挂在鞍鞒上,从内衣袋里摸出用黑色条绒做的早已褪去光泽的烟袋,卷了一支烟递给我。
“谢谢,我不会。”
“那是1978年,”他贪婪地吸了一口,然后将烟徐徐地喷吐出来,话随着烟一道从嘴里冒出来,“全队社员用粉碎四害后迸发出来的激情挥洒汗水浇灌出将近一千多亩地的山地冬麦,正值银毡连着金毡,沉甸甸、齐刷刷的麦穗耀眼夺目,大家怀着美好愿望开镰待割时,想不到一场鼠灾从天而降,仅仅一夜工夫,麦田里就只留下炷香似的光秃秃的麦秆……”
“那,后来呢?”我真不敢想象,小小老鼠竟有这么大的能耐,迫不及待地插了一句。
“嘿……”托克托拜惨淡地笑笑,“开春后,没有籽种怎么办?柴油用什么钱来买?机耕费、管理费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时候地还没有分呀,人们的心头更是蒙上了一层忧虑和积愁。您说,眼看火烧眉毛怎么办?咳,遇到这样的事神仙也退避三舍哪!大家只好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伯奇春身上。”
“那时候,他刚刚当选队长,几百双眼睛盯着他,好像他身上能长出麦子、流出油似的。”
“这也难怪。”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兴致勃勃地通知全队社员开会,两眼闪着充满希望的光,我还以为他在哪里喝了两杯呢……他站在灯前,环视一眼那一张张挂着痛苦的熟悉的脸,语气虽然和缓但十分有力地说:
‘乡亲们,现在怎么办?就是说今天明天我们该做些什么?难道几百双眼盯着遍地是冰雪的土地能长出粮食来吗?不能啊,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着那一块地,应该再往前看一点,往前看,看见什么啦?对,应该往山上看……’咳,下面又开热锅了。”
“他这是说啥呀?听了半天我也糊涂。”我莫名其妙地苦笑一声,问了一句。
“哈……”没想到托克托拜却出乎我意料仰天大笑起来。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很窘迫。
“您呀,记者同志,真够意思。”他用手背擦擦笑出来的泪水,“山里什么宝贝没有?”
“……噢,原来如此,高见,高见。”
“可您别逞能,在当时谁敢想这个点子呢?难怪他的这番话像一块火种,立刻温暖了大伙儿冻僵的心,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激动的泪花。”
“真是危难见人心哪!”听了托克托拜的话,我也很激动,两个眼角热乎乎的。
托克托拜收敛了笑容,低着头用鞭杆在鞍鞒上轻轻地敲打几下:“第二天黎明头一阵鸡鸣刚过,伯奇春就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队办公室。他卷了一支烟,抬起头,望着我们说:‘俗话说一个棚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叫大家来是打算搞点副业收入缓缓急,争取时间,一开春就能不失时机地下种,不知您们怎么想?……’好半天,我哥哥……是的,他叫库西尔拜,懵懵地问了一句:‘您叫我们念哪个经呀?’您猜他怎么说,咳,他反而哈哈大笑,弄得我们几个哭笑不是。笑够后,他叫我们互相看看,不看则已,一看都愣了!您说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们几个在座的都是队里有名的猎手哪!”
“猎手?啊?!……上山打猎?”我脱口而出。
“对,对,您猜对了。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组织一个打猎小组,上南山打野猪,打狼,夹狐狸,拾鹿角,既支援国家,又解决眼前的困难,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吗?”
“好主意,好主意。”我高兴得大声喊起来,马一惊,差点儿把我摔下来。
当我俩兴高采烈地谈论之际,两匹马驮着我们早已穿过几道山坡,一片鹅绒般的开阔地,盘着一条羊肠小道,直入一截峡谷。一阵清脆悦耳的流水声使我收住了缰绳,托克托拜走近溪边下了马,那马不等主人松嚼铁,就把头有力地向溪水伸去。那清澈见底的雪水,在阳光照射下,泛起花纹般的微波闪闪发亮,宛如天真的孩子在嬉笑,在向我们招手。这时,我仰起脖,抬眼往两边仔细瞧:那美丽的、绵长的峡谷从我们的马蹄下开头,带着肃静神秘的色彩,沿着灌木丛生的山脊,怪石嶙峋的绝壁向南蜿蜒而去。座座山峰插进了云端,从西边飘来的缕缕白云徜徉在碎光闪烁的皑皑白雪间,使人眼花缭乱。那背面的一片片苍翠雪松悠悠在巅。在一块悬崖上,一块巨大岩石伸首俯瞰,似乎随时都会从半空中向我们砸下来。岩石边垂下来的长长的一条条葛藤像翡翠珠帘似的吊挂着,不远处一株爬地松,枝干伸展,傍石倒挂。
托克托拜缓缓地走过来,把两匹马的缰绳熟练地缠结在一起,松一下肚带放开,停了片刻,又举起鞭杆指着前面的一座高峰说:“您瞧,就是那一座,像一位苗条的少女,对,是的,在峰腰伸出来的一株爬地松,像少女腰间的飘带,看见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是不是也有优美的传说?”
“我们出了牛录后,五个轻装猎骑就是沿着这条沟,顺着这条路进山的。那时,大雪封住山口,积雪埋没了路径,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两边陡峭的山壁悬着积雪,似乎只要喊一声就会崩落下来把我们淹没,听老人们讲,要是遇到雪崩喜鹊也难飞出去。狭隘的路又弯弯曲曲,有些地方马蹄踩上去就坍塌,有些地方由于白天阳光的照射和夜间的冰冻,雪的表面结成一层冰,马匹常常滑倒,令人毛骨悚然。走了一天,人困马疲,偶尔抬头寻见从大雪下面劈出来的苍葱的松枝,才能使被雪光刺痛的眼睛得以瞬间的慰藉。眼看太阳落山了,—阵阵迎面吹来的穿胸的寒风使人不断地打寒噤,迫使我们在一个失修多年冬窝子的东倒西歪的篱笆前卸了鞍。夜间天气虽冷,五个人紧紧地挤在—起,把雅尔哈抱入被窝里安然入睡了。”
“雅尔哈是谁呀?”我原来只听说五个人,现在又冒出个雅尔哈,急忙问。
“嘿嘿,是伯奇春的猎狗。”
“猎狗?!……哈,它在山上能干什么呢?”
“噢,您可别小看它,它可是救过伯奇春的命哪!”
“真的?”
“我怎么能骗您?有一年,我们过伊犁河到大布村诺罗(在水定县内)打猎,碰上一头几次挨枪未倒的艾吐浑(五岁的公野猪,獠牙最锋利)。那可是见人就追,见马就挑,红了眼的最凶残的家伙。真凶啊,不过片刻连挑三匹马,一个断了前腿,一个肠子全都出来了,一个胸部被劈开两半……这时谁还敢再近前哪,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它一撅一撅地跑去。正当大伙准备收缰时,突然从侧面飞出一骑,直射野猪。人们定睛看时,见一猎犬已近野猪尾,那家伙被逼得激怒了,大吼一声,猛地转过身向骑者扑来。骑者巧妙地转了一个弯,没想到马腿被苇丛绊了—下,一头栽过去,人早已离了鞍……当我们赶到时野猪已近伯奇春,伯奇春扑在雪里,野猪骑在伯奇春身上,只要动一下就会被劈成肉酱的。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只猎狗箭一般蹿跳过去,一口咬住了野猪的两个露在后面的红红的睾丸,拼出命往后撕扯。这下野猪可受不了啦,痛得嗷嗷吼叫,发狂似的扭头扑来,可是像被钉着似的,无论艾吐浑怎样猛跳还是旋风般的团团转,猎狗就是死死咬住不放。最后,艾吐浑筋疲力尽,一屁股蹲在地上,这时伯奇春突然跳将起来,瞅个准,抬手就是一枪。那猪足有二百八十三公斤。”
“啊!……想不到一条猎狗竟能救一条人命。”
“那时,雅尔哈刚满一岁,这样的狗真是少见。它是本地种,个子高大、瘦削、嘴尖,耳朵挺长,全身白中带黄,尾巴像马鞭,跑起来简直可以说是飞。从此,伯奇春无论到哪里,雅尔哈都一步不离,在猎场上立过不少奇功。”
“难得,难得。”
“第二天清早,一群山雀叽叽喳喳的声音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吵醒。几只羽毛光滑的乌鸦,环绕着我们破烂的居所翱翔,眼睛总是贼溜溜地窥视掉在地上的几粒马料。我们吃饱喝足后,抽了一支烟,察看了一下各自的枪和子弹袋就出发了。这时,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过了三个坡沟,分成两路沿着第四个坡脊蹬石而上时,突然我哥和萨拉苏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急速地向我们招手。”
“看见什么啦?”我的心猛地一跳。急忙问。
“伯奇春和我立即弓着腰,穿过岩石间杂乱丛生的红柳,靠近了他们。萨拉苏向谷底努努嘴,我稍倾过身去往下一看……
“一头三岁牛般大的野猪正在乱石间拱来拱去,嘴里不断地嚼着草根,两侧交叉而生的锋利的獠牙随着上下颚的嚼动不时地剪磨着,闪着阴森森的光。全身的硬毛棕发红,油光闪亮。”
“嚯,真是好运气……可我听说野猪只要听到枪响,瞬间就能扑到枪口前,是吗?”
“是的。野猪不仅生性凶猛,而且疾如流星,不小心就会被它伤害,甚至性命难保。”
“呜?”我像是亲眼看见那头野猪似的不由得惊呼一声,手心都沁出了冷汗。
“伯奇春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山势,叫我们三个人分头守住上面两个山腰和谷峰,自己独自一人,领着雅尔哈迅速地跳跃着向谷底迂回而去,我隐蔽在一块拔腰而起的尖石块后面,守住谷口,睁着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谷底,不放过任何疑点。不一会儿,谷底出现了伯奇春精灵般的身影,他猫着腰借着一石一丛,一步一步,渐渐地逼近了野猪。我心头一颤,全身好像缩起来,沉不住气了。……咳,我虽然是个猎人,可步行打野猪还是头一次,哪能不紧张呢?我正想喘一口气,镇静一下自己,只见雅尔哈像—支箭向野猪射去。那家伙突然见一只狗扑来,忽的一下,唰地竖起脊背上一绺钢针般的硬鬃,两只深陷的小眼闪着寒光,张开嘴,露出—副凶残的面目,猛然蹿出一丈多远,向雅尔哈反扑过去,雅尔哈一时退避不及,被挡在密密的红柳丛前,只听一声惨叫……”
“啊?”
“我们三个人大惊失色。慌忙提枪向下跑去几步一看,那发疯的家伙根本不理雅尔哈,一块巨石般地冲着伯奇春疾速滚去。”
“你们怎么不开枪呀?”我急得身不由己,攥紧了两个拳头。
“刹那间,我们惊呆了!我想喊,喊不出来,一阵战栗掠过全身,冷汗从前额上涔涔地流了下来也不知道,当我们醒悟过来想开枪时,野猪已离伯奇春四五米了,我的心突然一紧,惊叫一声,拔腿就飞也似的往下冲去。就在这—瞬间,伯奇春一蹦而起,甩手就是一枪!呼……真险哪!我一下瘫在地上,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哪家伙随着清脆沉闷的枪声,蹦得一丈多高,然后重重地摔在石头上,挣扎着惨叫着,像一座小山头崩下来似的滚下涧去。”
“万一没打中就糟了。”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阵轻松驱走了心头的惊悸。
“会打中的,您别担心。只要他的枪响那是没有闪失的。您要知道,枪声未落他早已纵身跳到石头上。叫人担心的倒是我们,萨拉苏一下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着气。您不知道。这是我们猎人胜利后庆幸的一种少有的兴奋的流露呀!”
“太动人了,托克托拜!我要是在场,能分享这种自豪,不知心里该是多么的激动。”
“过了一会儿,伯奇春笑呵呵地上来了。他显得很轻松,看了看我们三个,狡黠地眨眨眼,就坐在我身旁向我伸手。我摇摇头,笑了笑,掏出了烟袋递过去。”
“那雅尔哈呢?”
“雅尔哈受了轻伤,伯奇春撕下衬衫给它包好了。看样子伤口不太深,下山前就全好了。”
托克托拜说着爽朗地笑起来。我急忙替他卷了一支烟递过去。他也不客气,接过烟,夹在中指和食指间,一丝青烟随着徐徐微风飘忽而去。
“以后几天,”他用手指弹弹烟头,然后喷了几口气,吸了一口,“我们打了不少山羊、黄狍、狐狸、旱獭,还捡到七八对鹿角。高兴之余,立刻动手捆成四捆,驮在两匹马上,让萨拉苏向牛录报告好消息去了。过了几天后,我们三个人正从对面向阳的南山沟穿过,走着走着,我哥突然用手挡住我俩。我们互相看了一眼,警觉地抬头向山顶看去,只见三头野猪正在鼓鼓地瞪着闪着蓝光的凶眼,好像在侦察着我们,时刻准备扑过来。我们立即就地趴下,将三支枪口悄悄地对准了伸出来的三个狭长的脑袋。您不知道,这家伙有一股顽强的耐劲,你不动,它也不动,你能坚持多久,它也能陪你多长时间。在焦急的煎熬中,我们对峙了半个小时,还不见它们退却。我急得立即打开保险,想赏它们一颗铅弹。伯奇春制止了。是啊,它在上面我们在下,打不好就会吃亏的。可是,我已经出了一身汗,再也憋不住了。伯奇春见我满脸的汗水,缓缓地翻过身去,右手悄然地摸到一块石头,靠在一块石头后面,将石头轻轻地向右侧投去,只听呼啦一声,三个家伙猛地甩过头去,飞也似的跑了。”
“咳,多可惜呀!”
“您别急。它们是跑不掉的。它们跑不久,我们三个人立刻沿着坡背迂回而上。走了一段后,我们三个分了手,伯奇春提着枪向山顶跑去,挡住去路;我哥和我相距五十米左右,沿着东西边坡脊搜索而上,一边疾走一边细心地察看沟里杂乱丛生的红柳、灌木、岩石间……走着,猛地听到‘在这儿!’一声喊叫,我一下闪到一块石头后,循声望去,就是刚才那三个家伙串成一气,像狂暴的恶魔发了疯似的向我哥直冲过去。我哥躲在一棵松树后面,枪口正对准奔在前面的那头。我看情况紧急,心里一慌,脱口而出:‘别开枪!快上树!’可是已经迟了。只听砰的一声,震撼山谷,不但没打中,三头野猪已经到了我哥跟前。我哥走投无路,被逼得丢了枪就往树上爬。可是,唉,真急死人,他的两条腿不知怎么蹬了好一阵,也没爬上一人多高。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野兽伤害呢?当时顾不了许多,蓦地拔腿就冲过去,一边跑一边开了两枪。这下可好了,给我哥解了围,我可倒霉了。三个家伙好像知道我还没有换子弹似的,突然掉过头来,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我先是一愣,接着就往石头上跑。当我跑近一块大石头时,后面连呼呼的声音都能听到了。”
“那您刚才开的两枪……”
“心里急,跑得又快,全飞了。”
“那后来呢?”
“我慌了,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脑子轰的一声,全身立刻缩得紧紧的,口都干了。
“我是扑倒在地啦,只听耳边‘叭’的一声,接着砰砰两声,一阵嚓嚓的声音,以后什么也听不见了。”
“嘿,您还真有两下子呀!那枪是谁打的?”
“没有一点趴地的本事就算不上猎人啦。哈……第一枪是伯奇春打的,接着两枪是我哥放的。他俩跑到我跟前见我还趴在地上,仰头大笑起来。我慢慢地坐起来掏出了烟袋。伯奇春卷了一支烟,递给我哥笑着问:‘库西尔拜,我还以为你不会上树呢,想不到您还真能爬树,就是两条腿不怎么灵活。’我哥听了又是一阵大笑,这笑声淹没了一切,驱散了一切,惊飞了宿鸟,吓走了野兽。您说,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快乐吗?”
“啊,是的,是的。”我好像听到了他们甜蜜的笑声。
托克托拜说着,慢慢收敛了笑容,眼光从我的肩膀上往前移去,两眼立刻溢出喜悦的光,一下站立起来,指
配送说明
...
相似商品
为你推荐

 占位居中
占位居中




 直播中,去观看
直播中,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