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7549576999
-
ISBN:
9787549576999
-
出版时间:
2020-01
上书时间2022-07-06
卖家超过10天未登录
手机购买
![]()
微信扫码访问
-
-
商品描述:
-
内容提要本书秉承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方法论,试图融通历史与当下,对明清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公产与福利实践进行个案研究,以阐明国家转型的历史实践逻辑。本书将政治经济分析和文化阐释结合起来对公产的制度发明进行整体解释,并视乡村福利为一个历史的文化实践过程。
目录目 录
第一章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1
一、 整体史与历史人类学|3
二、 在实践与象征之间: 历史的整体观|9
三、 整体社会科学: 历史人类学的知识论姿态|23
第二章“共有地”的制度发明|29
一、 “共有地”的词源及其解释意义|31
二、 三个维度: 产权、资源与习俗|33
三、 山川水草: 自然之物与文化之物|38
四、 作为“公”的地方: 祖先与神明的“治所”|56
五、 “集体”的地方: 道德、市场与国家|61
第三章“业”与“报”|69
一、 问题的提出|71
二、 “业”与“租”|74
三、 “报”: 风水、德行与“福利”|87
四、 讨论|99
第四章公产征收与国家政权建设|103
一、 从十五都到磡头区|105
二、 “死人往里抬,稻谷往外挑”|107
三、 “土改”中对祠产和庙产的处置|111
四、 合作化时期基层机构的设立|116
五、 历史的延续性: 宗祠和村学|118
第五章从社区福利到国家事业|123
一、 问题与视角|125
二、 “庙产兴学”: 从义塾、学堂到国民学校|132
三、 短缺福利: 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学|141
四、 成为国家事业: 从集资办学到免费义务教育|147
五、 讨论|152
第六章集体产权实践与村庄治理困境|163
一、 问题|165
二、 沪郊农村集体产权实践|168
三、 农家生计的转型|179
四、 村庄治理的困境|188
参考文献|200
后记|218
部分章节 “庙产兴学”是清末以迄民国时期贯彻始终的“社会工程”,其实践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均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但又有其不同的制度和表述面向。这一“社会工程”不仅关涉教育史和宗教社会史,更整体地呈现了由“晚期中华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政治史。
“庙产兴学”的标志性事件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98年7月10日)光绪帝所下的一道“上谕”,即“各省府厅州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上谕并命令“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1]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是直接针对同日康有为所上奏折而发的,康有为在奏折中明确提出将各省书院改为中学堂,乡邑淫祠改为小学堂的主张,“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2]而洋务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则早在这年的四月(戊戌三月),即写成了《劝学篇》,其庙产兴学的主张与康有为相比,更具操作性,“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而“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为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3]
两人“庙产兴学”的主张并不仅仅在于对学堂经费筹措的焦虑,更在于各自背后的文化观[4]。我们且不论康有为“中学西学并用”、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只就庙产兴学策论中的“废淫祠”说,也表现了儒学正统性的关怀,还是有着相对一致的共识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礼部祀典“正祀”的强调和保护,而在于将学堂经费的筹措和废淫祠[5]的文化政治结合起来了。如此,则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之前无论是佛教寺观还是民间祠宇[6],似乎于办学无甚作为甚至全无兴趣,其实不然。有关佛教经济史研究表明,佛教寺庙庙产来自民间、官府乃至皇室捐输、布施者众[7];相当多的民间寺庙由几个村落或宗族联合修建,庙产也由宗族和村民捐助,本属地方公产[8]。至于宗族设学田办义塾,宗族村落修社学、开书院,更是宗族史上的经常性事业[9]。
即是说,戊戌维新运动之前,祠堂和民间寺庙兴办义学就已大量存在。而且动员和整顿民间庙宇田产兴办义学,甚至成为地方衙门的一项行政职责。清代道光和同治年间,直隶州深州府在张杰和吴汝纶为知州时,官府对庙田进行了整顿,以用于筹措义学办学经费。同治年间深州府知州吴汝纶如此记载:“道光初,张杰为州,悉括境内废庙田,得五千四百四十余亩,增立义学至二百四十五区,定师范五章,学规制九十六章,集录学田亩为书,于是州境义学为天下最。然杰周防官吏而不检士民,及道光之季,义学大抵皆废,豪民私攮学田,弊端朋一生,不可究诘矣。汝纶在州,以为学散在四境,兴废自由,官不能遍知,又无良师长董之学虽多,几于村村有学,实乃连数村无识字之民,则上务为名,下私其利,不责实之过也。于是言于上官,请检视学,审废者,没入其田,以为书院田。居一岁,书院增田一千四百十九亩有奇。”[10]根据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直隶深州的官府乡土调查,深州有义学的村庄较多,且大多设在庙宇中,如西阳台村两座义学,分别在村内的三官庙和三义庙中;大魏村义学两座,其中之一在村南庙后;东阳台村义学在村东头路北白衣庵庙;亦有数村有多座庙宇而无一座义学者;亦有若干村庄村内庙宇数座,而义学设于民宅者,如河栏井村[11]。清代前期直隶畿辅的很多义学正是因为资金缺乏,无力大规模修建校舍,往往借助寺庙或祠堂作为办学场所,并以庙田租谷作为经费来源;山东地区的诸多义学亦设于寺庙道观,且有籍没庙产以创设义学的记载[12]。
庙产兴学中的庙产转为学款及儒教正统化的表述,均表现了历史的连续性,而非传统的断裂。庙产兴学的关键在于筹款占用庙产的规模超过以往,兴新学聘用师资也存在困难,即如张之洞所指陈的,是“延师”与“筹款”二事。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庙产兴学政策随之搁浅。与“庙产兴学”的上谕仅隔七十八天,光绪帝不得不发布新诏:“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祠,著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致于民情不便。”[13]时隔仅三年,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推行“新政”, 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该社中学堂, 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4]于是“庙产兴学”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进入实践的轨道。庙宇改为学堂,仍是延续了一定的历史传统,光绪末年、宣统年间的许多官府“视学”、“劝学员”视察属地各村小学堂情形,及发现相当数量的小学堂设在关帝庙、娘娘庙、火神庙、龙王庙等民间庙宇中[15]。如前文所述,庙产兴学的最大困难在于筹款,仅仅将庙产转为学款,尚不敷使用,清政府于是又增加了学捐这一新的财政项目。为此而激起了民众的抵抗,各地的“毁学”事件此起彼伏。时人有评论说:“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亦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又见矣。考其原因,无非为抽捐而起。”[16]
如果说清代前期的庙产用于兴办义学,乃基于村落社区公产办公益的道义经济逻辑,那么清末新政庙产兴学中学捐的设立,则显示了国家权力经由县衙而渗透到村落社会[17]。庙产兴学的筹款模式还只是相对表层的变化,而围绕着筹款所进行的制度安排及权力运作机制,则显示了新的实践面向,即劝学员和学董制的设立。在提取庙产为学款的过程中,由行政系统(劝学所)任命的学董与掌管庙产的会首、庙首也会产生诸多纷争,如梁勇的研究所呈现的个案,清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巴县麻柳场学董田翰卿建议将朝音寺、自生桥庙产提作学产,这一倡议道道了庙首田荣升等人的反对,双方遂起讼争,巴县县令的批词称,“所禀为真,当属可行。 该学董即俟视学到境,面议举(证?)可也。”显然是支持学董田汉卿一方。梁勇由此认为:“既有以庙首/会首为管理核心的地方共产管理体制,逐步被学董为代表的新式教育行政体系取代,庙产/会产也因此完成了它的控制权的转移过程。”[18]所谓新式教育体系是否由此脱嵌于民间宗教而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事业呢?恐还不能妄下结论。
史实证明,民国时期庙产兴学的权力运作机制仍未发生根本变化。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庙产兴学”在政策层面有一些调整和变化,显示了国家权力的现代化努力仍不脱历史连续性的窠臼[19]。北洋政府时期的政策举措与清末新政有着很强的历史连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袁世凯的个人作用有关。袁世凯虽然是扼杀戊戌维新的“功臣”,但也是推动清末新政的重臣,北洋时期的袁世凯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政策[20]。1914年,教育部颁行“整顿教育方案草案”,极力强调地方筹集学款之必要性:“学款之缩减,至今日而极矣……若本地方原有公款公产,应先行收入充用。先之以劝导,继之以奖励,庶人知兴学为地方之责任,即划定地方税时,学款亦不至漫无着落,此实根本之计画也。”[21]所谓原有本地方公款公产,在乡村主要是指祠产和庙产。
浙江省松阳县佳溪村,于清光绪三十年(1906)成立震东初等小学堂,校舍系借用该村刘氏宗祠及禹王庙左厢共二十八间。宣统元年(1908),劝学员范晋巡视该学堂,对于该学堂冠名“公立”,如此评述:“惟该学堂常年经费系由各村乐捐,故名公立震东小学。本届所颁戳记,除去‘震东’二字,改称官立,名实未免不符。”[22]校名中的“公立”,实反映了佳溪村人对于学校公产性质的认知。该学堂的创办人系该村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刘厚体,亦即范晋巡学时所说的堂长。据叶哲铭的田野调查,“公立震东初等小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由寺庙田产、佳溪村及周边大石、后周包、邓村等村庄大姓的祠堂田产、私人捐赠三部分构成,其中刘氏宗族早年捐赠给附近万寿山望松寺的70~80亩田产是最大一宗,而望松寺被当地人称为佳溪刘家的“小祠堂”[23]。祠产与庙产的财产边界相对模糊,学产来源的社区公共性由此可见一斑。该村同年还成立了“私立震东女子两等小学堂”,学堂经费主要来自刘氏信房中二房的田产,校舍则是刘厚体名为“一亩居”的大宅院。学堂设有校董会,刘厚体的族兄刘厚和、刘厚生都曾任学董,且由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教员也由刘氏族人担任,学生只招收刘姓宗族的女子。所谓“私立”,在学堂经费来源及招生对象上主要限定在刘氏一族范围内,女子小学堂学产来自于某一房支,而全宗族女童均享有就学福利,则于全宗族而言,又系公产。
民国十四年(1925),两所学校合二为一,名第五区震东小学校,学产系“抽拨寺租九十一担四桶,殷户捐租六十七担。”[24]合并后的震东小学校由徐仁基(刘姓姻亲)任校长,邻近乡村学生多来升入高等班级就学,男女学生计百余人。1940年,学校更名为“佳溪中心国民小学”,邻近的庄山、资口、交塘口、后周包、李顶、杨村头、赤岸、半胡、上坞源、大石、狮子口等村的适龄学童,均来就读。1943年以后又由毕业于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刘厚体之子刘福穰任校长[25]。由学校名称的变更,可以看出佳溪村震东小学办学实践中“国家的在场”,但是由清末至民国初年,学校公产的寺产、族产的合一及刘氏宗族对于校产籍校务的控制,则是一以贯之的。刘厚体系前清秀才,又到日本留过学,尚具有旧乡绅的身份特征,而其子刘福穰则主要是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新派人物。不管怎样,佳溪震东小学的控产机制还不能轻易说发生了所谓的“权势转移”,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揭示学董、校长的身份与权威,更在于透视祠产与寺产作为办学经费来源,折射了宗族与民间信仰的结合这一村落及村际社会的合作机制。
乡村学校控产机制背后所隐含的是地方社会结构的特定模式。与浙江地区有所不同的,在广东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单姓聚居村,这些宗族大都拥有大规模的族田[26]。在清末民初的所谓庙产兴学运动中,华南宗族更多的是延续此前族田办族学的传统,虽然有时可能利用庙宇作校舍,但族田仍是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广州番禺县龙眼洞村[27]系一樊姓聚居村,龙眼洞村按习俗分为中、南、西、上四个社。清末民初,各社太公(宗族)竞相拨款建造书塾,专收本房子孙读书。书塾多用祖宗名字命名,如中社有致和、有和、德焰、德炳书塾。民国八 年(1919),龙眼洞村创办了至德国民小学,因校舍是由一洞樊公祠“至德堂”出资兴建,故以“至德”作为校名,而招收学生不分房支,开设六个班级,共一百多人就读。至德学校收取学费,但较富裕的房支,本房子孙学费由宗族公尝负担,直到小学毕业,如上社西奥公祠一族便是如此。此外,该村另一房支宝峰堂每年都拨钱给学校,以补充学费不足。学校实行校董制,校长选村内德才兼备者担任,第一任校长是樊家治[28]。村志中虽无校董会名单,但可以推断,校董会成员基本是由龙眼洞村樊氏各房支族老组成。至德学校的成立,实际上是将各房支书塾整合起来,形成新族学,这样的新族学,则可能成为宗族新的权力中心[29]。但以学堂或国民小学形式出现的新族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宗族权力结构,而只是强化了宗族长老对公产的支配权。
[1] 迟云飞编写,《清史编年》第十二卷,光绪朝(下)、宣统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版,第92页。
[2] 康有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康有为全集》第四卷,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页。
[3] 张之洞,《劝学篇》,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1页。
[4]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对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庙产兴学思想做过专门的比较研究,认为“立孔教为国教”是康有为庙产兴学的核心理念,借此实现儒教的一元化支配地位;而张之洞的庙产兴学主张则更多的是从地方实务官僚的立场上构想出来的、较为现实的振兴教育的手段,参阅[日]村田雄二郎《孔教与淫祠——清末庙产兴学思想的一个侧面》,见[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想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0页。
[5] 废淫祠的儒学正统化运动,自宋以迄于明清,即不绝如缕,明洪武年间魏校的“废淫祠”折是标志性事件,日本史学家井上彻对此作过专门研究,参阅[日]井上彻《魏校的捣毁淫祠令研究——广东民间信仰与儒教》,《史林》2003年第2期。
[6]佛教寺庙与民间庙宇的分类,大致相当于杨庆堃所说的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参阅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7] 参阅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8]参阅杨联陞《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的四种募钱制度》,见氏著《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9] 参阅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10] (清)吴汝纶纂,《深州风土记》,记四·学校,同治十年(1871)纂,光绪二十六年(1900)文瑞书院刻本。
[11] 王庆成编,《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649~668页。
[12] 分别参阅赵振丰《清代畿辅地区义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第39页;徐海峰《清代山东地区义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第45页。
[13]迟云飞编写,《清史编年》第十二卷,光绪朝(下)、宣统朝,第117页。
[14]迟云飞编写,《清史编年》第十二卷,光绪朝(下)、宣统朝,第262页。
[15] 参见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43页。
[16] 《毁学果竟成风气耶》,《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时评,转见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228页。
[17] 参阅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8] 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9] 许效正对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政策做过系统研究,参阅许效正《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1895~1916)》,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0] 参阅陈志让《袁世凯传》,王纪卿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1]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22] 范晋,《松阳县各学堂调查表》,《浙江教育官报》,宣统元年(1909)总第8期,转引自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第118页。
[23] 叶哲铭,《底层视野——现代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生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93页。
[24] 吕耀钤修,高焕然纂,《松阳县志》,教育志·学校教育,民国十五年(1926)活字本。
[25] 刘为绾纂,《佳溪刘氏宗谱》(下册),松阳,未刊稿,1999,转引自叶哲铭《底层视野》,第195页。
[26] 参见[香港]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27] 该村在民国时期隶属番禺县第四区、第七区,今属广州市天河区。
[28] 广州市天河区龙眼洞村民委员会编,《龙眼洞村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1、172页。
[29] 参阅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作者简介 张佩国,1966年9月生,山东成武人,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学术兴趣集中在中国乡村产权和福利文化研究。出版《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财产关系与乡村法秩序》《林权、坟山与庙产》等专著四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二十一世纪》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
孔网啦啦啦啦啦纺织女工火锅店第三课
开播时间:09月02日 10:30
即将开播,去预约


直播中,去观看

 占位居中
占位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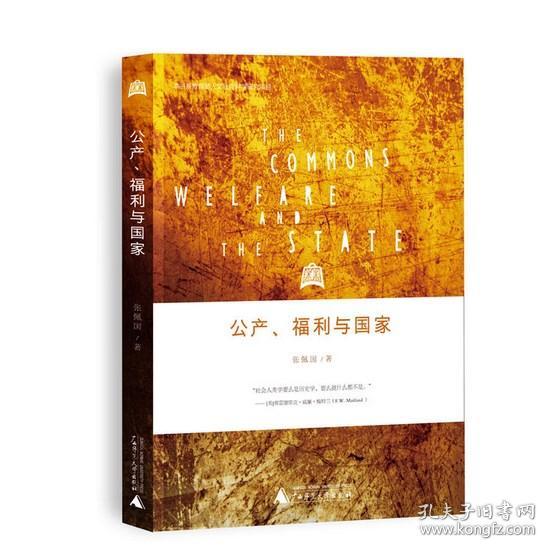



 直播中,去观看
直播中,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