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上海博物馆在处理抄家物资出口的把关工作中,多次遇到有白蕉先生为金学仪所作梅花题跋的作品。因金学仪这个名字名不见经传,画坛也没听说过此人,甚为疑惑,几经询问,不得其解。一次工作人员正好问到白蕉先生的老友郑为先生,这才知道,金学仪者,白蕉先生之夫人也。这是学仪夫人文革後与郑为先生重逢时,郑先生亲口所言。
金学仪女士(一九二年六月七日——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原名金惠慈,上海青浦县崧泽村人,今闵行区崧泽村。自幼颖悟开朗,用她自己的话来讲,下得了田垄,上得了纺机,识得了文丰。儿时在私垫念书,因家境尚佳,年青时入上海师范读书:一九三一年二十岁毕业,随即在上海金山县张堰镇小学教书。命运也让她教了一辈子的书。在张堰镇教书的那段日子裏,邂逅年青英俊的白蕉先生,对他的儒雅、才学留下深刻印象。邂逅为缘份播下了种子,虽然其後有近五年并不联系,但五年後,金学仪女士在上海陕西南路的步高里创建“全人小学”,并当校长。全人小学离当时白蕉先生上班的《人文月刊》的社址不远,两人又碰上了,爱情的种子终於萌发生长。虽然金学仪女士知道白蕉先生的家庭情况,尤其是他的婚姻情况,非常同情他的抗婚与无奈,也非常理解他的痛苦,但这一切并没有阻碍这对情侣感情的发展。经过家庭会议,她终於与白蕉先生走到一起,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恋爱史。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在上海南京路邓脱摩饭店举办婚礼。对白蕉先生而言,他结束了孤独地住在宿舍裏,一个人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也从此结束了,像是获得了重生:於是“复生”、“复翁”的落款出现在了他的作品中,并用了一辈子。对他而言,金学仪女士象天使,这种爱是刻骨铭心的。
作为中国现当代书法史 “海上”帖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白蕉以其醇正的二王书风与深刻的书学见解,为打破碑学独尊天下的格局和恢复帖学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的作品也对当代书法产生深远的影响。白蕉先生的传世作品以行草居多,楷书较少,篆隶书则更少。其行草以二王为宗,清隽秀朗、淳淡婉丽、潇洒俊逸,直入山阴堂奥。《白蕉金学仪梅花书画册》,是白蕉先生与其夫人金学仪先生难得一见的书画合璧册,白先生书咏梅诗,金先生图之以梅花书画皆清雅绝俗,难得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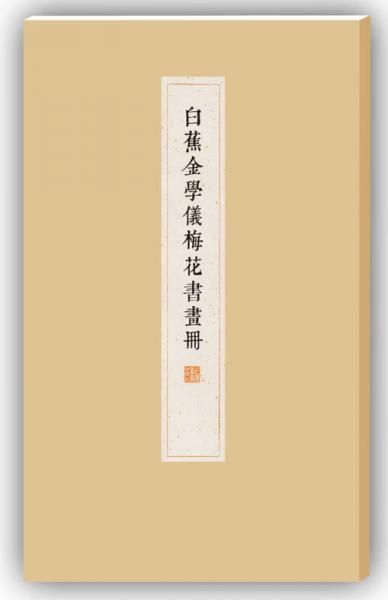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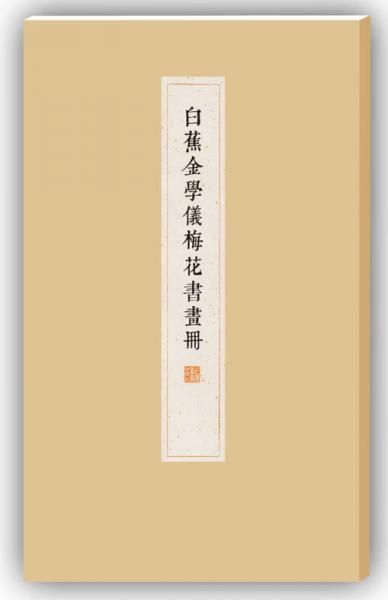
 直播中,去观看
直播中,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