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张燕瑾 著
-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ISBN:
9787509770856
-
出版时间:
2015-01
-
版次:
1
-
装帧:
精装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394页
-
字数:
99999千字
-
作者:
张燕瑾 著
-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ISBN:
9787509770856
-
出版时间:
2015-01
-
纸张:
胶版纸
-
页数:
394页
-
字数:
99999千字
售价
¥
58.00
4.9折
定价
¥118.00
品相
九五品
上书时间2024-04-26
卖家超过10天未登录
手机购买
![]()
微信扫码访问
-
-
商品描述:
-
基本信息
书名:张燕瑾古典文学论集
定价:118元
作者:张燕瑾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1-01
ISBN:9787509770856
字数:467000
页码:394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
编辑推荐
《张燕瑾古典文学论集》中的每个作家,甚至每篇作品都有不同的创作个性,解读这些作品也应当是个性化的,这些文章显示了论文作者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个性。
内容提要
本书既有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对戏曲小说散曲诸文体的宏观思考,也有对作家作品、创作风格、题材演变的论析,对名作中关键词语、关键人物的考辨,提出了独到见解。作者用文学之眼解读文学现象,与那些把文学当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献学等的视角不同。每个作家,甚至每篇作品都有不同的创作个性,解读这些作品也应当是个性化的,这些文章显示了论文作者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个性。
目录
作者介绍
序言
序 宁宗一
几天前燕瑾突然来电话,说他走进南开已经55年,离开南开整整50年了,听了这话,我的心为之一震。50年,55年,就这么过去了!他感慨万端,我则浮想联翩。在岁月匆匆中,我何尝不是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个“热血老人”。而燕瑾从首都师大文学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年复一年,也加入了我们退休的行列。燕瑾话题一转,希望我为他的新作写则小序,我没有理由推却,我何尝不想借序言谈谈我和燕瑾的那份儿缘。 下面就先说“情”,后讲“理”。 在南开中文系我曾教过1956级、1957级、1958级的“宋元文学史”,其间有着密集的政治运动穿插其间,最突出的当然是“反右”和“拔白旗”,它们都是整肃知识分子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在这种肃杀的氛围中,心灵已被扭曲,情志更加杂乱,虽然尽力想把课讲得好一些,但已力不从心了。“幸运”的是,到了给燕瑾的1959级讲宋元文学史和元曲专题时,已是三年困难的末期了。在吃不饱肚子到能将就吃得好些时,我与1959级有缘相遇了。此时有一个“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出现在我们面前,直到今天仍值得深长思之。正题:1958年的大折腾,“共产风”劲吹,国人被煽动得似乎就快要进入天堂了,但全国性的大饥荒很快来临,全民忍饥挨饿,个别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反题:吃不饱,只好休养生息,大的政治运动暂时消歇。虽然吃不太饱,又少油水,上课站着讲,腿打哆嗦,然而内心却获得几分松弛,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党群之间出现了少有的平和,这可能是燕瑾在本书后记形容我笑口常开的原因吧! 其实,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是一个常被“误读”的青年教师,那时没有今日之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所以对我这样的人就从“误读”发展到“污名化”。然而幸运的我竟相遇了1959级!这个年级相比而言没有1956级那么多的“调干生”,大多数是从高中直接升上来的,绝大多数同学勤奋好学,性格开朗,充满朝气,其中还真有几位颇有灵气的、能安静地读些书的“读书虫子”。而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有些松动,特别是有几位不嫌弃我的、“警惕性”不高的同学,常来我宿舍走动,或是一块儿到华粹深先生家去听老唱片儿,有的同学还能跟我一块儿去看戏。我似乎又享受到些许“单纯”的快乐。对,至今我还不时追怀那段“单纯”的日子。像燕瑾来我家谈的就是他的读书心得,就是切磋古典小说戏曲中有意味的问题,比如我1961年开始写那篇万言长文《浅淡中国戏曲艺术发展规律》,其中有些是吸取了燕瑾的意见,少了些错误的。几十年来,心中浮起的生命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和快乐,常常带给我绵长的慰藉。我要感谢燕瑾和他们年级的另外几位单纯的同学,他(她)们成全我年轻时的单纯,并把它变为行动,而从来未去计量得与失。燕瑾,我真的怀念咱们那时的单纯。也许是因为今日之光怪陆离的社会,已经让人唯恐不复杂了!功利意识充满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上有多少虚伪、假象?!难道我们不是更加怀念那时的单纯吗?人的成长、人格的养成,乃至生存空间,不是太需要这种单纯吗? 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对1959级毕业时的具体情况没有丝毫印象,是不是那时我到唐山地区的抚宁县搞“四清”去了?只是后来我知道燕瑾到北京任教。那时在北京有我的家,父母健在,每当回京省亲,总要到燕瑾的家做客,日久天长,我们真的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认识的燕瑾是一位真正讲文化坚守与自我完善的大学教师。有一点我们是如此相似:从1963年开始我一直在南开从事教学,燕瑾在首都师大一呆也是五十多年。我们都没有被众人趋之若鹜的“热门”工作所诱所惑,都没有在逆境中退缩和放弃我们应坚守的教师的岗位。所以见面时仍然一如既往,不谈人事,少言政治,只谈本行的学术,交流信息,分析热点问题,且真的做到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有认同,有争议,又在争论中获得撞击后爆发出来的思想火花,而共享其幸福。 燕瑾的自我完善是他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妻子把一个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不说,而且对燕瑾照顾得无微不至。因此我一直认为,燕瑾的步步攀升,就有一半是他夫人的功劳;进一步说,燕瑾的学术成就是和这个“安静”的家分不开的。安静乃是一种状态,一种情志,安静就成了燕瑾心灵的常态。他的内外环境让他能安静地读书,让他能安静地书写,也让他能安静地进行教学。一本好书就能让他安静下来,写一篇文章也能让他安静下来,安静就是这样成为他的内心生活。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出版了《唐诗选析》,稍后又和他的同窗好友杨锺贤合著了那么厚厚一册《唐宋词选析》。我想这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永不动摇的不为外界诱惑的内心生活。比照燕瑾,我的缺失就是在家在外都没有一个安静下来可以自处的空间,正如法国伟大作家蒙田所说:人的最大灾难是回到家还安静不下来(大意)!我可能就是一个没能安静下来的教师,我真的缺乏这种生命状态和内心的安静! 我的父母相继去世,我觉得北京没有了我的家,我很少回北京了,与燕瑾聚会时间也少多了,只是他还不时来校担任博士生的答辩主席,我们的交流似少了些,但是电话中还是不时要谈谈各自的心绪,交流一些学术研究的点滴心得。 作为一名教师,除了屋中有些纸本参考图书外,我拥有的财富只是一届又一届理解我、关心我、维护我的同学。至今我把他们视之为我生命中最丰厚的精神财富。我感谢他们,也惦念他们,并以他们为骄傲,这其中就有燕瑾在。 下面该说“理”了。我是认真读过燕瑾很多代表性著作的,所以敢于冒昧地说,我能把握他的学术策略、研究方法以及他的治学风度。 燕瑾在他的新作“后记”中说了不少给我鼓劲儿的话,我只有惭愧二字。但是,由字度人,却百感交集。首先要交代的是,很多高校文科朋友都有印象,在1979年南开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古典戏曲小说研究室,且创获颇丰。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的几位恩师华粹深先生、王玉章先生、朱一玄先生和许政扬先生就已在讲课和辅导研究生时渗透了一种理念:中国的古典小说与戏曲必须互相参定,同步研究。几位老师身体力行,用自己的研究业绩证实了这一点。华师在讲明清戏曲时,专门开了《红楼梦》专题课,而许先生则有黄克兄编的《许政扬文存》存世,其中从辞语考释到文本研究,都是把小说与戏曲紧紧结合起来进行相互参定的研究。直到1979年华先生在小说戏曲研究室成立会上的讲话,也是围绕这一问题,阐释这一学术理念的。后来我把它浓缩为:一部戏曲史就是一部活的小说史;一部小说史就是一部活的戏曲史。老师们的这一理念与实践经验,后来成了南开小说戏曲研究文脉中的一项学术方略,它始终让我牢记在心,不敢稍有忘却。 可是,华、王、朱、许开创的这条学术文脉到后来就中断了,我在写我的《心灵投影》一书的编后赘语时说的那段话,确实发自肺腑,觉得有负先师的重托。可是,今天在给燕瑾写书序时,重温了他的新作与旧著,在我脑海中翻腾又冷静而仔细地统计了一下,南开中文系的学子能把小说与戏曲同步研究的为数不多,即使有几位很有成就的博导,往往也是单打一,当然这有学养、路数和兴趣追求的多重因素在。但是把小说戏曲同步研究作出实绩,而且有声有色地又被精神同道首肯,我想,燕瑾兄应当是其中之一吧!此点绝非虚妄之吹捧,请看,燕瑾从小说观念、戏曲审美、乐感文化到作家与文本研究,再到断想、随感、辞语考释以及经典文本的新校注,真是涉猎极广,全面开花!燕瑾用力勤,也获得了相应的收获。再举一例,请读者不妨翻看他的《从平民到英雄》一文,燕瑾全然没有停留在题材层面上比较研究,而是直抵作者之文心,又从文体内涵中的深隐层次上加以把握,从而开发出小说戏曲之异同。我的授业恩师、著名相声与戏曲作家何迟先生在1951年与华师合讲“人民口头创作”课时,何迟师提出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说: 形式就是限制,限制就是思路。 今天重温先生的教导,意识到水浒题材演变中,除了都是表现世道人心,除了再次看到小说与戏曲之血缘关系以外,也让我们看到二者在艺术功能上的大不同。剧曲之张力和动作的直观性,远非小说叙事文字所能比肩,而小说的铺叙的弹性和衍生之诸多细节和设置长短不等的对话,也非剧曲所能全然做到。所以,戏曲与小说各自的优势和“被”规定的“限制”也往往影响各自作者的内涵指向。燕瑾对《桃花扇》的解读、对唐传奇的诗性分析、对《西厢记》的讲解等,都可以看出他是从文心与文体两个层次上进行思考的学术思路。燕瑾进行过其他文体和文化研究,也是为探讨戏曲小说与其他文体的关系所做的学术拓展。提出这些问题,意在说明,能够继承南开小说戏曲研究文脉的燕瑾兄乃是真正的持守者之一。 作为一种学术方略,戏曲与小说的同步研究尚有诸多难点。从深隐层次上去观照戏曲与小说的内在关系,就有太多有待认真探索的课题。要而言之,如从艺术文化学角度与艺术形态学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就有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亟待从理论上、史料上加以破译。且不说二者属于两种文类,仅就叙述体和代言体等文体类型来考察,我们就已感到本体研究中的交叉渗透的复杂性。好在我们有先贤为我们铺路,又有时彦为我们提供了思路,我想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小说、戏曲观念的同一性,它们的异质同构,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燕瑾和我都表明我们是文学本位和文本主义的坚守者。我们的坚守,也许是意识到了要继承老师们给我们奠定下的基石;也许是我们科研与教学体验之所得;当然也有几分想把南开的文脉延续下去的期许;但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审美精魂对我们心灵的滋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和文学的历史学研究。我们只是不赞成抛弃文学本位的为考证而考证,并认为只有考据才是真学问,进而排斥或低估文学审美的研究,对于这些过于偏颇的议论,理所当然,我们难以接受。其实钱锺书先生早在上世纪就有言在先:“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与黄克兄的个人通信中,还感叹文学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的附庸,“而不能自立门户”。钱公的“自立门户说”,真乃一种文化焦虑。 我们不否认,目前文学研究中提出的综合研究、学术史研究、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界限。燕瑾和我的文化焦虑是:当前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小说戏曲研究,有一种取消“文学性”的倾向,而对文学性即对文学特质的任何消解,都是对文学本体的戕害。一个时期以来,“文学”被泛化了,小说、戏曲也被泛化成无边无际的“文化”,或者别的什么,那最终是导致文学审美性的消解。我们的忧思是:当人们不再沉浸在诗意世界去领略那天才的文学精魂和美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大幸还是不幸?令人鼓舞的是,燕瑾全然没有对文学的审美感悟失去耐心,他从未把小说与戏曲只当作社会历史的脚注,而是文学性的研究和审美批评的强化。请读者再翻阅他的《元剧三家风格论》、《混阳蒸变奈何天》、《历史的沉思》、《东泰西华各争奇》等佳作,你可以发现燕瑾都有对作家的机锋顿悟、妙谛之艺术把握,而对作品所显示的天纵之神思,幽光之狂慧的诗情阐释,读后令人神旺。 至于燕瑾和我如此强调回归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是因为我们真切地感悟到文本才能真实地反映作家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宁肯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认识作家,从文本给人类感情世界带来的审美启示和艺术贡献来评定作家与文本的价值。《戏曲研究》第59辑载邓黛《近十年来〈桃花扇〉研究综述》有一段话可以印证燕瑾的治学思路: 与以上这两种看法不同的是一种“心灵史”说。张燕瑾先生《历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桃花扇》不是反映南明历史,不是在总结亡国教训,“它超越了浅层次的功利目的,没有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也不是写宗教,七位‘作者’是避世而居的贤者,而不是斩断世情的道徒,侯李入道也只是理想破灭后的迷惘困惑,‘非入道也’。作品追求的是富有哲学性的悲剧目的而不是历史目的。作者只是借历史的框架抒写‘天崩地解’历史巨变之后对士林群体人格的反思,成为吴敬梓的先导”。“作家是在用心灵感悟历史,借历史抒写心灵,写对人生对历史对社会的探求,充满天才孤寂之感和痛苦的沉思。”这种既不同于将《桃花扇》当作历史政治教科书的传统观点,也不同于过于走极端的宗教主题说的观点,在各式各样的“主旨研究”中显得十分冷静而客观。这种观点抓住了研读作品的关键所在,强调作者的人格、心灵、理性反思对于作品的影响。这种对于个人心灵史的关注研究(而非社会化、泛化的研究)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这是对燕瑾学术追求的判断和评价,也是对新世纪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的展望和期盼。 我读燕瑾的论著,有一种默然契之的感觉。比如,我们在面对文体时都注意设身处地,都讲究以心会心,我们都力图把阅读经典文本看作是一种纯真的审美体验,因为我们感悟到了作家的心灵文本正是饱含着人生和审美体验的。于是在我们阅读与书写时竟发现我们的审美体验与作家的体验灵犀相通了。正是基于会心与比心,我们才能有沟通,有交流,有对话,这可能就是陈寅恪先生点拨我们的“了解之同情”之要义吧! 燕瑾说他已经七十有五的高龄了,这也让我一惊!燕瑾也这把年岁了!我们也许没有诗样的人生,但是燕瑾却有他的诗样的文字。燕瑾的人生态度是平和,内心的平和,于是书写的文字也是平和。然而他的平和文笔除文采斐然以外还灌注着思想,他的人生态度与理论思维体现出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旺盛!他的系列专著证明,在安静与平和的心态下,他始终孜孜矻矻地从事学术研究,这在我们学术界也属少见。也许他感悟到了文学与科学之异:科学是越近越看得清,而文学则是越远才能越看得清。燕瑾的学术青春正步人老年时,却有了更多的文学发现,所以他不敢也不愿稍作停顿,而是永握书写的笔,而且有了更多的可写的审美发现。 作为独立学人的燕瑾竟然和我这样的老人都进入了老年期,在回归心灵、审视自己时,我发现,我们的书写何尝不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过程?是的,真正的学人是注定要有所追求的,我们坚守的依然是精神劳动,而且企盼自己的这份儿劳动能够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我冒着有互相吹捧之嫌的危险,写就了以上的文字,我真诚地希望读燕瑾这本书,又捎带看了我这篇小序的朋友,能够相信一个已经八十三岁的老人,是没有时间去编造瞎话的了。
2013年11月11日午后

![]()
孔网啦啦啦啦啦纺织女工火锅店第三课
开播时间:09月02日 10:30
即将开播,去预约


直播中,去观看

 占位居中
占位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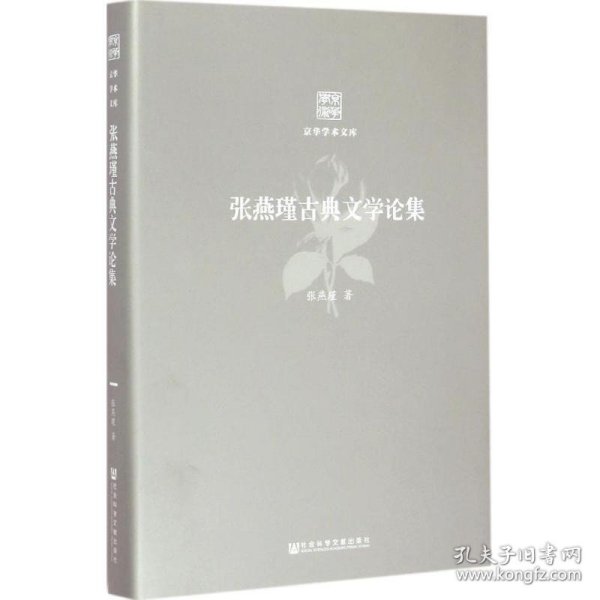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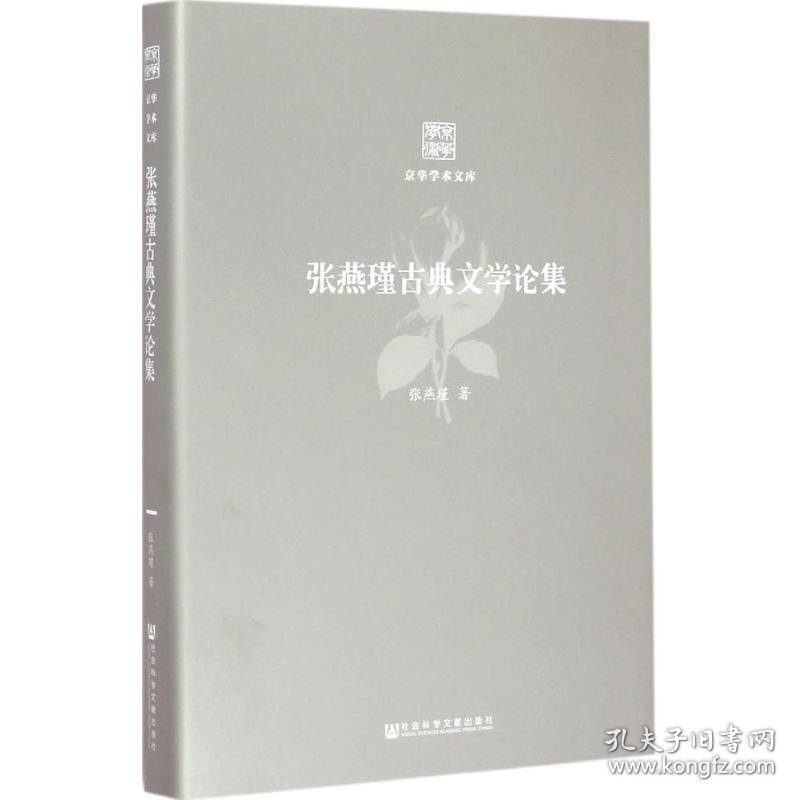
 直播中,去观看
直播中,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