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附和的黄宫绣!该书根据亲身临床用药实战,对《本草纲目》错讹,混淆,进行订正,删繁撮要,故冠以“求真”。简明扼要,切合临床实用,使本书有三十几种刊行版出现,纸贵一时。本书取乾隆三十九年文奎堂刻本,精校而成——本草求真 ——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清代御医黄宫绣 著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0-1-A】
举报
上书时间2020-05-25
卖家超过10天未登录
-
-
商品描述:
-
【本草求真】
,12卷,一作10卷。清代黄宫绣(锦芳)撰。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作者深研药理,“俾令真处悉见”,故以“求真”名书。前9卷收药520种,正文药条按功效类药,每药直叙性味、功效,兼论药物来源、真伪及炮炙法。作者论药,喜用简明言词,直述己意。其论药理,“总以药之气味形质四字推勘而出,则药之见施于病者,既有其因,而药之见施于病而既有效者,又有其故。”从而将药理、药效与药物形性及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确有新见。此书采用了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检索方法。其正文分为补剂、收涩、散剂、泻剂、血剂、杂剂、食物等七大部,书后附“卷后目录”(即索引),各药名仍按草、木、果、谷、菜、金、石、水、土、禽、兽、鳞、鱼、介、虫、人等分部。前后目录及正文药条下均注有序号,颇利查找。书前载图477幅,多从《纲目》与《本草汇言》两书中转绘。
【成书背景】
黄氏有感于当时本草书多“理道不明,意义不疏”,况有“补不实指,泻不直论,或以隔一隔二以为附合,反借巧说以为虚喝”的现状,乃力纠时弊,集平素之治验,采百家之精萃,著成《本草求真》十卷。
【流传版本】
现存乾隆三十四年(1769)初刻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以及民国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
【作者简介】
黄宫绣(1720-1817)字锦芳,江西省宜黄县棠阴君山人。清代著名医学家。乾隆时代宫廷御医。与陈自明、崔嘉彦、严用和、危亦林、龚廷贤、李梴、龚居中、喻昌、谢星焕并列为江西历史上十大名医。
黄宫绣出身儒医世家,天资聪敏,自幼对医药之学情有独钟。他搜罗医书,潜心钻研,凡有“一义未明确,一意未达,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杂,概为删除……,断不随声附和,主张该病必先明脉理,治病必先识药性,尤应注重实践,探求真理”。他治学严谨,务求实际,平生为众多病人治疗疑难病症,均卓有成效。他是乾隆年间的御医,对宫廷珍藏的各种医学专著以及秘方、验方,无不悉心研究。既不泥古薄今,也不厚今废古,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虽精研脉学,仍主张四诊合参,反对单凭脉断病。临症之余,根据古典医籍,参与历代名医学说,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写成《脉理求真》3卷,《本草求真》10卷,《本草求真主治》(又名《锦芳医案》2卷),《医案求真初编》(又名《医学求真总录》)5卷刊行于世。
《脉理求真》较详细地介绍了脉诊部位和各种脉象的主病,并论证了各家的论说。他结合自己的经验,注释了《新增四言脉要》、《十二经脉歌》和《奇经八脉歌》,并附有《脉要简便须知》,对脉法中的某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作了扼要论述,是学习和研究中医脉法的参考资料。此书和他的《新增脉要简易便知》解放后多次再版。
黄宫绣有感于当时本草书多“理道不明,意义不疏”,况有“补不实指,泻不直论,或以隔一隔二以为附合,反借巧说以为虚喝”的现状,乃力纠时弊,集平素之治验,采百家之精粹,著成《本草求真》10卷,付梓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本草求真》是一部研究药物学的专著,该书于药物意义“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说,概为删除,俾令真处悉见”,故冠以“求真”之名。系对《本草纲目》删繁撮要而成,影响较为广泛,简明扼要,切合临床实用。全书共10卷,书中选载常用药物520种,按药物品性分成若干类,详述其形态、性味、功效、配伍、制法及与各种疾病的关系,便于读者对药物性能进行分析比较,是研究中药的重要参考资料。新中国建立后多次再版发行。
史料记载编辑
黄宫绣(1730—1817年)字锦芳。清代江西宜黄人,享年八十七岁。宫锈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向习举子业,尤专心致志钻研医学,是我国清代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宫绣学问渊博,对医学有较高深的造诣,他根据《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古典医籍的理论,参考历代名医的学说,结合自已的见解,著书立说。其治学严谨,凡有“一义未明,一意未达,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杂,概为删除,……断不随声附和”。特别是他注重实践,探求真理,故其著作,概以“求真”冠名。如《医学求真录》、《脉理求真》、《本草求真》。其研究本草,论述药性,也是“每从实处追求,既不泥古薄今,复不厚今而废古,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这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为后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学术论文
【内容简介】
本书载药520味,分上下两编,上编对药物的形态、性味、功能、主治以及禁忌,记载甚详,下编分列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和药物总义三部分,该书于药物意义“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说,概为删除,俾令真处悉见”。故冠以“求真”之名。
对于药物的分类,黄氏颇具独到之处。他没有采用历代本草诸书所延用的部属分类法,亦即将药物以草木谷菜金石等为编次,而采用药物功效分类法,按药物之品性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七类,各类又分为若干子目,如补剂中又分为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等;泻剂又分为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等。于每味药下面注明该药的部属和卷首目录序号,这可谓是本草著作中很有进步意义的索引形式,不仅便于查阅,而且有助于学者辨析药物的异同,指导临床遣药组方。例如,山药和白术虽同属补剂,但山药为平补,白术为温中,临床运用,自当有别。
在用药法象方面,黄氏根据五色入五脏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学术见解,提出以形、色、性、味来区分用药。认为“凡药色青、味酸、气臊、性属木者,皆入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凡药色赤、味苦、气焦、性属火者,皆入手少阴心、手太阳小肠经”;“凡药色黄、味甘、气香、属土者,皆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经”;“凡药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者,皆入于手太阴肺、手阳明大肠经”;“凡色黑、味咸、气腐、性属水者,皆入于足少阴肾、足太阳膀胱经”,并明确提出药有“形性气质”、“气味升降浮沉”、“根梢上中下”、“五伤”、“五走”、“五过”。这些认识,为药物的功效和临床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黄氏十分重视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对成无己、张洁古、朱丹溪、李东垣、李时珍、喻嘉言等人的精湛论述一一采撷,然却师古而不泥。如《本经》谓白茅根能“补中益气”,黄氏却不以为然,他说:“至云能以补中益气,虽出本经,然亦不过因其胃热既除而中气自复,岂真补益之谓哉。经解之论,似未可信。”此说颇为成理。另外,对于前贤之言,黄氏也不盲目崇拜。如张洁古、李东垣、朱丹溪咸谓黄柏为滋阴之品,后人遂翕然学之,视为补品。黄氏却力驳其谬,认为:“黄柏性禀至阴,味苦性寒,行隆冬肃杀之气”,“奈今天下之人,不问虚实,竟有为去热治劳之妙药,而不知阴寒之性能损人气、减人食,命门真元之火一见而消亡,脾胃运行之职一见而沮丧,元气既虚,又用苦寒,遏绝生机,莫此为甚。”此精辟的论述,对喜用苦寒,欲通过“坚阴”而收补益之功的医者,无疑于当头棒喝。
有些药物的某些性用十分相似,极易混淆,黄氏通过辨析,力求尽得深蕴。如麦冬与天冬均属养阴清热之品,但黄氏强调“麦冬甘味甚多,寒性差少,天冬所主在肺,而麦冬所主在肺,更在心”。半夏与贝母皆能祛痰,但“半夏兼治脾肺,贝母独清肺金;半夏用其辛,贝母用其苦;半夏用其温,贝母用其凉;半夏性,贝母性缓;半夏散寒,贝母清热,气味阴阳,大有不同。”另外,辨芍药赤白之异,赤者能泻能散而白者善补善收,分当归有头尾等,皆予以详论。凡此种种,体现了黄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黄氏在长期的临证中,还发展了一些药物的新功能。如对“刘寄奴”一药,除点明其具有破瘀通经行血的功用外,还指出该药用于金疮出血,可使血顿止。也实为黄氏的经验之谈。
对于药物的来源、真伪和炮制,黄氏也十分重视。如谓“山西太行新出党参,其性止能清肺,并不能补益,与久经封禁真正之党参(人参)绝不相同”。防风以“北出地黄润者佳,泗风车风不堪入药”等。对药物的炮制,强调“制药贵乎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并把药物配伍理论引伸为“以药制药”的炮制方法。以黄连为例,就有十种制法:“心火生用,虚火醋炒用,胆火猪胆汁炒,上焦火酒炒,中焦火姜汁炒,下焦火盐水炒或童便炒,食积火黄土炒,湿热在气分吴茱萸炒,在血分干漆水炒,眼赤人乳炒。”这些叙述,对在中药炮制方面,颇有实践意义。
【影响评价】
《本草求真》的特点在于切合实际,不尚空谈,是一部医药学紧密结合、内容精简扼要、临床实用价值较高的本草专著。
[1-5]

![]()
孔网啦啦啦啦啦纺织女工火锅店第三课
开播时间:09月02日 10:30
即将开播,去预约


直播中,去观看

 占位居中
占位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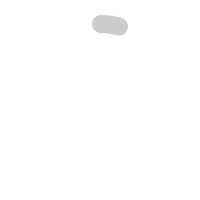
 直播中,去观看
直播中,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