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可开发票,请放心购买。
-
作者:
编者:周啸天|责编:刘姣娇
-
出版社:
四川人民
-
ISBN:
9787220122750
-
出版时间:
2021-05
-
装帧:
精装
-
开本:
其他
-
作者:
编者:周啸天|责编:刘姣娇
-
出版社:
四川人民
-
ISBN:
9787220122750
-
出版时间:
2021-05
售价
¥
68.28
7.4折
定价
¥92.00
品相
全新
上书时间2023-09-12
卖家超过10天未登录
-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周啸天,号欣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研究员,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所获其他奖项有《诗刊》首届诗词奖第一名、第五届华夏诗词奖第一名、2015诗词中国杰出贡献奖。
目录
卷一 五言古诗
张九龄 感遇十二首之一
张九龄 感遇十二首之三
陈子昂 感遇三十八首之一
陈子昂 感遇三十八首之二
孟浩然 秋登兰山寄张五
孟浩然 彭蠡湖中望庐山
孟浩然 夏日南亭怀辛大
孟浩然 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
王维 陇西行
王维 渭川田家
王维 西施咏
李白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李白 月下独酌四首之一
李白 关山月
李白 子夜四时歌之秋歌
李白 子夜四时歌之冬歌
李白 长干行
李白 春思
杜甫 望岳
杜甫 赠卫八处士
杜甫 新安吏
杜甫 石壕吏
杜甫 新婚别
杜甫 羌村三首之一
杜甫 羌村三首之二
杜甫 羌村三首之三
杜甫 梦李白二首之一
杜甫 梦李白二首之二
韦应物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韦应物 长安遇冯著
柳宗元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柳宗元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孟郊 游子吟
孟郊 秋怀十五首之一
李贺 咏怀二首之一
李贺 感讽五首之一
刘驾 贾客词
聂夷中 伤田家
卷二 七言古诗
卷三 五言律诗
卷四 七言律诗
卷五 五言绝句
卷六 七言绝句
附录
内容摘要
本书乃《唐诗鉴赏辞典》主编周啸天教授精选唐诗300首而成,对比前人版本,本书中选采了许多不见录于其他版本的作品,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刘希夷《代白头吟》,七言律诗之“尤要者”,如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许浑《咸阳城东楼》,以及中唐诗人“尤要者”李贺的作品,等等,弥补了遗珠之憾。同时,为了便于广大唐诗爱好者研读作品,本书对所涉及引用诗文、点评一律随文注明出处,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意以及拓展知识,是唐诗爱好者研习唐诗的案头书。学习唐诗,不仅仅在于学习与诗歌相关的知识,而在于感悟诗歌的美,并将这美深深化为自身对世界的观照,把诗歌的美从文字中复活于现实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得到唐诗的精髓。
精彩内容
卷一五言古诗感遇十二首之一 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远离城市的寂静的山林中,芳草香花生生不息。春天里的兰叶茂盛,秋季里的桂花芬芳。春兰秋桂本不希求别人的赞美,然而,兰桂的芳香随风传播,引起了志趣高洁的人们的爱慕,他们不辞辛苦,踏遍山隅苦苦寻求。春兰秋桂终于被列入名花的光荣榜,虽然这并不是它们所要追求的目标。修养使人趋于美善,荣誉毕竟是身外之物。 这是张九龄自明品节之作。张九龄是贤相,也是盛唐初期的五言名家,在唐诗发展过程中地位很高,影响深远。他被贬到荆州以后,写了十二首《感遇》,是一组五言古诗,表现了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诗风一洗六朝铅华,质朴刚劲,寄慨遥深。 这是第一首。取意屈原《离骚》:“不无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以兰、桂自比,以美德自励。全诗的主旨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二句,意谓贤者志洁行芳,无须求人赏识,博取高名,表现了作者坚贞耿介的品格。前人说:“曲江公(即张九龄)诗雅正沉郁,言多造成道,体含风骚,五言直追汉魏深厚处。”(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全诗只是平平道来,不激不厉,看似毫不经意,而深刻的思想自寓其中,令人含咀不尽。 感遇十二首之二张九龄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这是一首歌咏丹橘的诗,其实也是托物咏志。屈原有《橘颂》诗,赞美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有坚贞不移的美德。诗人也是南国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贬所荆州又多橘,因此自然受到了屈原诗歌的影响,写下了这首诗,可以说是张九龄的“橘颂”。 其他树木一到秋天就会落叶,而橘树却经冬不凋。可见并非江南有什么暖冬,而是橘树禀性耐寒。常绿的橘树不仅可供观赏,而它的果实红橘,实在是味道鲜美而营养丰富的水果。用来款待贵宾,是摆得上桌面的佳品。想不到有人只取桃李,而排斥红橘。这样做公平吗?诗人当时被贬荆州,而荆州盛产红橘,故以此自喻;诗中说桃李乘时,则暗指李林甫、牛仙客等小人得志。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较屈赋有新意。一是用具有“岁寒心”的松柏来相比拟橘树,强调其独立不移的品格;二是指出其果实的珍贵,暗示积极的用世精神;三是以桃李来反衬,指出其被忽视的作用。这样,更能启人想象,委婉深沉,意蕴宽广。诗中也有对自己遭受贬谪的抱怨,对命运无常的悲叹,但整个精神却是积极向上的,再加上语言的清新简练,平和温雅,历来受到传诵。 卷二七言古诗登幽州台歌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本篇抒发了一个巨人的孤独感。事由:公元697年营州契丹叛乱,武攸宜亲总戎律,陈子昂参谋帷幕,军次渔阳。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子昂料敌决策,直言进谏;武氏愎谏,但署以军曹,掌记而已。子昂因登蓟北楼,感昔乐毅、燕昭之事,作此诗(参见唐代赵儋为其所撰碑文)。蓟北楼即幽州台,遗址在今北京市。 昔燕昭王欲雪国耻,思得贤士,郭隗进策道“欲得贤士请自隗始”,燕昭王遂在易水东南筑台,置千金其上,招揽人才,遂得乐毅等。诗人登楼,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群雄割据的时代,眼前的原野上曾活动着燕昭王、乐毅等一批杰出人物,君臣其为相得,可谓圣贤相逢。诗人不禁为自己出世太晚,未能赶上那个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惋惜:“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燕昭王》)“前不见古人”五字中包含着具体、复杂的思想内容,感喟沉痛。 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日子,今后也许还会有。然而诗人又感到去日苦多,恐怕自己等不到那激动人心的未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一何幸,遂起黄金台。”(《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郭隗》)——“后不见来者”五字,在前句的基础上加倍写出生不逢时的孤独和悲哀。 “念天地之悠悠”是写诗人面对空旷的天宇和莽苍的原野,不禁生出人生易老、岁月蹉跎的痛惜与悲哀。无限的时空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逼出一个“独”字,叫诗人百感交集。于是在前三句的无垠时空的背景上,出现了独上高楼,望极天涯,慷慨悲歌,怆然出涕的诗人自我形象。一时间古今茫茫之感连同长期仕途失意的郁闷、公忠体国而备受打击的委屈、政治理想完全破灭的苦痛,都在这短短四句中倾泻出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而富才能之士遭受黑暗势力压抑的悲哀和失落感。 这首诗直抒胸臆,不像《感遇三十八首其二》那样含蓄委婉,却更见概括洗练;不像《燕昭王》《郭隗》那样具体,却有更大的包容。诗的内涵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怀才不遇,而具有更深广的忧愤——一种先驱者的苦闷。正如易卜生说:“伟大的人总是孤独的。”(《人民公敌》)此亦即鲁迅说的在铁屋中最先醒来的人所感到的苦闷。《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正是在抒写屈子苦闷的诗句中,我们找到了陈子昂诗句之所本。 它有力地表现了一种烈士的惨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意义同价值的人所说的话。老先生说这话时心中的寂寞可知!能说这话的人是个伟人,能理解这话的也不是个凡人。目前的活人,大家都记得这两句话,却只有那些从日光下牵入牢狱,或从牢狱中牵上刑场的倾心理想的人,最了解这两句话的意义。因为说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同懂这话的人生命的耗费异途同归,完全是为事实皱眉,却胆敢对理想倾心。”(沈从文《谁的生命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它还成功地表现了一种哲理的思索。“短短二十余字绝妙地表现了人在广袤的宇宙空间和绵绵不尽的时间中的孤独处境。这种处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触和境况,而是人类的根本境况,即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的境况。”(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对短小到二十二字的一首诗的意蕴探究的不可穷尽,充分说明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功。至于在形式上,前二整饬而后二则纯用散文化句法,诗的散文化即口语美,这种写法,完全是服从于内容的需要的——只有冲破过于整齐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现一种奔迸而出的不平之情。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春江花月夜》本乐府《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旧题,最早见于陈朝。陈叔宝(陈后主)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春江花月夜》与《玉树后庭花》是其中最艳丽的曲调(参见《旧唐书·音乐志》)。隋及唐初犹有诗人,然皆五言短篇,在题面上做文章而已。吴中诗人张若虚出,始扩为七言长歌,且将自然景物、现实人生与梦幻融冶一炉,诗情哲理高度结合,使此艳曲发生质变,成就了唐诗最早的典范之作,厥功甚伟。 《春江花月夜》属于“四杰体”,是卢、骆歌行的发展,故亦曾随四杰的命运升沉,从唐到元被冷落了好几百年,直到明前七子领袖之一的何景明重新推尊四杰后,它才被发现,被重视,被推崇至于“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的高度。“大家”,在古代文学批评术语中是超过“名家”一等,指既有杰出成就又有深远影响的作家。四杰就不曾得到过这样的荣誉。《红楼梦》中林黛玉《代别离》一诗,就“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诗曰《秋窗风雨夕》”。也可见它所具的艺术魅力。 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本身就足以唤起柔情绮思。可同样是这五个字,在陈后主笔下只能是俗艳浅薄的吟风弄月——其辞虽与时消没,但从《玉树后庭花》可得仿佛:“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然而在张若虚笔下则完全不同。其根本的差异就在诗是沉湎于肤浅的感官刺激与享乐,还是追求深刻的人生体验之抒发。大诗人与大哲人乃受着同一种驱迫,追寻着同一个谜底,而且往往一身而二任焉。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泰戈尔的诗篇里,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喟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也属于这个行列。它与其说是一支如梦似幻的夜曲,毋宁说是一支缠绵深邃的人生咏叹曲。 从诗的结构上说,《春江花月夜》不是单纯的一部曲,而是有变奏的两部曲。在诗的前半,诗人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沉思着困扰一代又一代人的根本问题。与众不同的是,张若虚将这一沉思放到宇宙茫茫的寥廓背景之上,放到春江花月夜的无限迷人的景色之中,使这一问题的提出,更来得气势恢宏,更令人困惑,也更令人神往。 张若虚并没有采用石破天惊的提问式开篇,如“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屈原《天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李白《把酒问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水调歌头》),而是从春江花月夜的绮丽壮阔景色道起,令人沉醉,令人迷幻。这似乎是一个优美的序曲。隋炀帝已经写过:“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春江潮水连海平”似乎就是从这里开始。潮汐,本是日月与地球运行中相对位置变化造成引力变化导致的海水水位周期性涨落现象,吴人张若虚是熟悉这种景象的。月圆之夜,潮水特大。大江东流而海若西来,水位上涨,遂成奇观。这里写春江潮水而包入“海”字,使诗篇一开始就比隋炀帝诗气势更大。本来是潮应月生,看起来却是月乘潮起;不说“海上明月共潮升”而说“海上明月共潮生”,一字之别,意味顿殊,使习见景色渗入诗人主观想象,仿佛月与潮都具有了生命。 “滟滟”是江水充溢动荡的样子。月光普照与水流无关,诗人的主观感受却是月光“随波千万里”,水到哪里月到哪里,整个春江都洒满月的光辉。“千万里”“何处无”,极言水势浩远,月色无边。由一处联想到处处,诗人情思也像潮水般扩张着、泛滥着。以下由江水写到开花的郊野,过渡自然轻灵。“月照花林皆似霰”,月下的花朵莹洁如雪珠,吐出淡淡的幽香,写出春江月夜之花的奇幻之美。春夜何来“空里流霜”?明明是月光造成的错觉,故细看又不觉其飞。“汀上白沙”何以“看不见”?那也是因为一天明月白如霜,淆乱了视觉的缘故。 这两节写景奇幻,真有点令人目迷的感觉,诗人又并未迷失在镜花水月的诸般色相之中,而独能驭以一己之情思,一忽儿又跳脱出来。纷繁的春江景物被统摄于月色,渐渐推远,“看不见”了。诗人于是由色悟空。 被月光洗涤净化的宇宙:“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如此光明清澈的环境,让人忘掉日常的琐屑烦恼,超越自我,而欲究宇宙人生之奥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前句可以解为:江畔人众,何止恒河沙数,谁个最初见到这轮明月?就今夜而言,此问偏于空间范畴。后句则言:江上之月番番照临人寰,然不知青天有月自何时,江畔有人又始自何时,人与月的际遇又始自何时?此问则偏于时间范畴。由此看来,这是两个问题。但前句亦可不限于此夜,可以解为:代代江畔有人,究竟何人最早见到这轮明月?换言之亦“青天有月来几时”(李白《把酒问月》)也。由此看来,这又是同一个问题,以唱叹方式出之。通过“人”见“月”,“月”照“人”,反复回文的句式造成抒情味极浓的咏叹,令人回肠荡气。 诗人浮想联翩,产生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思想:“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有限与无限这对范畴,很早就有诗人在咏叹,与张若虚同时代的刘希夷也有咏叹。这仅仅是“天地终无极,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翻版么?否。虽然同样是对有限无限的思考,“岁岁年年人不同”着眼于个体生命的短暂,而“人生代代无穷已”着眼于生命现象的永恒,前者纯属感伤,而后者则是惊喜了。代代无穷而更新,较之年年不改而依旧,不是别有新鲜感和更富于生机么!生命现象,你这宇宙之树上茁放的奇花呀!无数个有限总和为无限而又如流水不腐。这是诗人从自然美景中得到的启示和安慰。诗中的“江月”是那样脉脉含情,不知送过多少世代的过客,它还来江上照临,还在准备迎新。皎皎的明月,你这天地逆旅中多情的侍者呀!闻一多说,诗人在这里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对每一个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唐诗杂论》)。如果我们把哲理与诗情分别比作诗之骨与肉的话,《春江花月夜》绝不是那种瘦骨嶙峋的哲理诗,更不是那种骨瘦肌丰的宫体诗,相形之下,它是那样的骨肉匀亭,丰神绝世,光彩照人。 在诗的后半展示了一个人生舞台,咏叹回味着人世间最普遍最持久的见难恒别的苦恼与欢乐。别易会难,与生命有限宇宙无限是有关联而又不尽相同的事体。生有离别之事,死为大去之期,故生死离别,一向并提,这是有关联的一面。不过离别悲欢限于人生,而与自然宇宙无关,在视野上大大缩小范围,这是二者毕竟不同的地方。故诗的后半对前半是一重变奏。如果说前半乃以哲理见长,则后半就更多地具有人情味。在所有的情亲离别之中,游子思妇是最典型的一类。东汉《古诗十九首》已多有表现,论者多把游子思妇的苦因归结到乱离时代。殊不知夫妻情侣生离之事,乱离时代固然多,和平时代也不少。李煜的“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红楼梦》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咏叹的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现象。《春江花月夜》的后半就着重写和平时代的悲欢离合之情,对古诗词中游子思妇主题做了一个总结。诗人的特出之处在于,他运用了四杰体反复唱叹的句调,设计了许多富于戏剧性的情景细节,创造了浓郁的抒情氛围,在同类题材之作中可谓观止。 这部分一开始,诗人就描绘了一个典型的离别场所:“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浦”即渡口,为送别地点。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极目千里兮伤春心。”枫叶秋红,青枫是春天的形象。在此青枫浦口,见一片白云去远,更引起于离别的联想。以下就引入游子思妇之别情。“扁舟”在江,而“楼台”宜月,故诗人写道:“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谁家”与“何处”为互文,言“谁家”可见不止一家,言“何处”可见不止一处。这两句实是一种相思,两处着笔,反复唱叹,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二句同一机杼。 曹植诗云:“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七哀》)本篇写月夜楼台相思,实化用《七哀》句意。然而诗人却设计了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情节:“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思妇对着妆台,不能成寐,想要卷帘去月光,但帘可卷而月光依然,撩人愁思;思妇意欲捣练,误认砧上月光是霜,想要拂拭,结果却“拂还来”,拂了个空。这两句写思妇懊恼情态,极有生活情趣。那卷不去、拂还来的月光,实是象征思妇无法解开的情结,无法摆脱的愁思,有赋抽象以具象之妙。“可怜”“应照”云云,皆取游子遐想的情态,更有幻设之致。楼头思妇与扁舟游子虽非一处,此夜望月则同,却又信息难通。《子夜歌》云“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此则曰“此时相望不相闻”;《子夜歌》云“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此则曰“愿逐月华流照君”,皆辞异情同。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二句对仗精工,就表意来讲,却是模糊语言。“鱼龙”偏义于“鱼”,鱼与雁皆为信使。“长飞”“潜跃”云云,意言不关人意。“光不度”暗示音讯难通;“水成文”,可惜不是信字。两句诗尽传书信阻绝的苦恼。日有此思,则夜有此梦。“昨夜闲潭梦落花”,又模糊于主语,或云是思妇,或云是游子。其实两可。 诗的结尾最有意味,照应题面,逐字收拾“春江花月夜”五字。花落春老,海雾蒸腾,隐没斜月,而相隔天南海北的人儿不知凡几:“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尽管如此,却也必然有人踏上回故乡之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这个结尾之精彩,就在于诗人写够了人间别离的难堪后,又留下了会合团聚的希望。他并没有写到意尽,似乎更好。此生此夜,总有人乘月而归,在饱尝离别滋味之后,他们将得到重逢的喜悦,以资补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水调歌头》),这才是人生。这是继“人生代代无穷已”之后,诗人给读者第二次精神上的安慰。这也是自然美景给他的启示。唯其如此,这支人生咏叹曲才显得那么积极乐观、一往情深。明月在告别前留下深情的一瞥(“摇情满江树”),显示出造物对于人类的厚爱。 全诗以春江花月夜为背景,沉思着短暂而又无涯的人生,抒写着情侣间的相思别情。诗情的消长与景物变化十分协调。在诗的前半,读者看到了春暖花开,潮涨月出,以及夜幕的降临,渐渐引起哲理性的人生感喟。诗的后半,随着这种哲理感喟的生活化、具体化,读者又看到了春去花落,潮退月斜,而长夜亦将逝去。这绝不是一夜的纪实,而更像是人生的缩影。诗歌的形象概括力是很强的。李泽厚修正闻一多的说法道:“其实,这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它上与魏晋时代人命如草的沉重哀歌,下与杜甫式的饱经苦难的现实悲痛都决然不同。它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美的历程》)余恕诚先生把此诗与王维《春日田园作》并论,说:“《春江花月夜》从自然境界到人的内心世界都不受任何局限和压抑,向外无限扩展开去。人们面对无限的春江、海潮,面对无边的月色、广阔的宇宙,萦绕着绵长不尽的情思,荡漾着对未来生活的柔情召唤。”(《唐诗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它与其说是初唐诗的顶峰,毋宁说是盛唐第一诗,春风第一花。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以孤篇压全唐。 卷三五言律诗春夜别友人二首之一 陈子昂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 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二首》约作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春天。于时诗人将告别家乡射洪,远赴东都洛阳,友人为之饯别,诗人感而为诗二首。这里选的是第一首。 “银烛吐青烟”二句从饯宴写起,用了许多华美的词藻“银烛”“青烟”“金樽”“绮筵”,极言饯宴档次之高。“吐”“对”两字,一动一静,暗示时光流逝,让人不免思绪万千。“离堂思琴瑟”二句,从饯宴写到送别,表现出诗意的跳跃性,而过渡相当自然。“离堂”为饯别的处所,“琴瑟”指朋友宴会之乐。语出《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琴鼓瑟”。诗人面对饯宴,想到明日长路漫漫,依依不舍之情跃然纸上。 “明月隐高树”二句,描写早行景色。晓风残月,银河渐淡,与今夜的欢聚一堂,别是一番滋味。有人批评说,佳句倒是佳句,然“明月”“长河”是秋景,不是春景。有人反驳道:不然,“隐”字内已有春在。其实,柳宗元便有“春半如秋意转迷”(《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之句,不可执泥而论。“悠悠洛阳道”二句,用“此会”二字绾住起处,言后会遥遥无期,表现出对家乡对友人的深切留恋。不胜黯然神伤,凄其欲绝。 从结构上看,可以认为全诗立足饯宴,以思写别;也可以认为全诗以“别路绕山川”为关捩,以前写饯宴话别,以后写别后相思。从声律上看,三句“琴”字当仄,七句“阳”字当仄。还有人指出,此诗“八腰字(每一句中间那个字)皆仄”,若不经意。作者并非不懂,而是不屑以辞害意。作者崇尚汉魏风骨,而此诗不废陈隋余习,唐人清旷一派,俱本乎此。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在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唐诗中,张九龄的《望月怀远》在屈指可数之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样的诗句是把天下人一网打尽的。就连诗中的月亮,可以是中秋的月,也可以是春月。这样的诗句属于任何时代,对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是家喻户晓的。“天涯共此时”写出了一种空间的距离和心理的认同——这是一个国家的认同、一个民族的认同。它还使人想起另一个天才的诗句:“别时容易见时难”(李煜《浪淘沙》)。当我们念起“天涯共此时”的时候,想到的正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这正是“望月怀远”的题中之意。张九龄本人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两句诗会如此这般地穿过了一千年的时空,成为联结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感情纽带,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魅力。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接着写月夜中人无尽的怀想。由于首联的关系,这一联消息甚大。“情人”不限于男女,可以推广到一切关系——亲子也可以、兄弟也可以、同志也可以、朋友也可以、祖孙也可以,凡是相互思念的人,都可以被一网打尽。而“相思”也不限于男女,而是形形色色的相互思念。连“怨”也不必是幽怨,也可以是“相思”的强化表达。在月下,“相思”被拉得很长很长、放得很大很大,“遥夜”“竟夕”的字面,“起”字的勾勒,状出绵绵不断的感觉。四句的音情是非常饱满的,与读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感觉,并无二致。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烛光下的环境是温馨的,适宜于亲密关系的。而月光,则是烛光的放大。诗中人吹灭蜡烛,在月光中徜徉。皎洁如银的月光让人低回不已,流连忘返,直到感到寒意、感到夜露的冷湿,才想起应该披件衣裳。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最后两句表达对

![]()
孔网啦啦啦啦啦纺织女工火锅店第三课
开播时间:09月02日 10:30
即将开播,去预约


直播中,去观看

 占位居中
占位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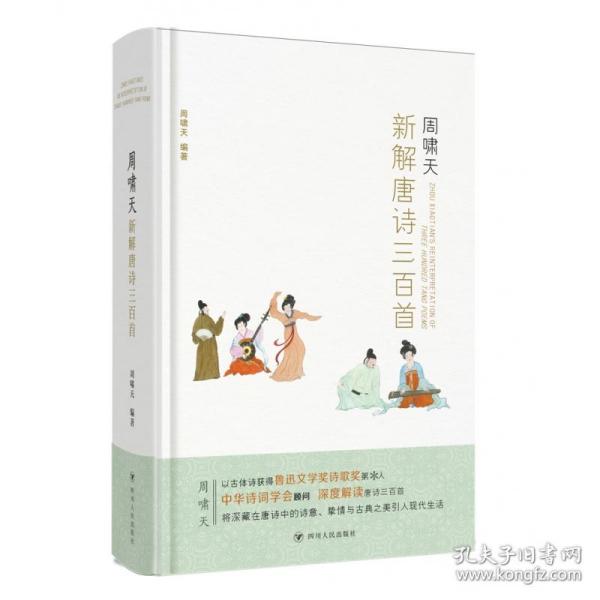


 直播中,去观看
直播中,去观看